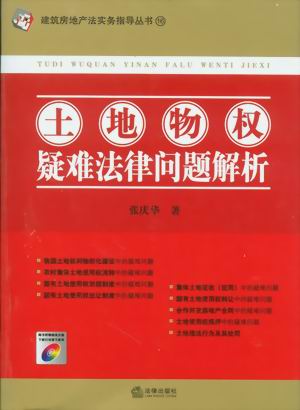
可以說,土地使用期限屆滿后土地使用權及地上物如何處置,一直是令立法者頭痛不已的難題。人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物權法》的制定上,然而《物權法》的規定看來仍不能讓人滿意。筆者認為,我們在立法時的思路選擇可能有問題,并對如下問題可能欠缺考慮: (1)當初《暫行條例》對不同用途的土地所規定的最高使用期限的依據是什么?比如,為什么住宅用地的最高期限是70年而不是50年或100年7汶一如此明確的量化標準是如何計算出來的?有何科學依據或法理依據?據說當初借鑒參考了香港的有關規定,可是中國大陸的土地制度和香港的土地制度有可比性嗎?如果這一期限的規定本身就缺乏合理依據,那么很可能這一規定本身就是錯誤的。就錯誤的問題怎么可能找出正確的答案和解決辦法呢? (2)當初立法者規定土地使用權的最高期限,其主要考慮的就是我國土地所有權不能買賣,能進行買賣和交易的只能是使用權,而土地使用權的交易是在所有權人保留所有權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這種交易具有明顯的租賃性質。既然土地使用權的出讓具有租賃性質,當然土地使用權作為出租物就不能沒有使用期限。 但是,如果強調土地使用權的租賃性質,則租賃期滿后所有人收回租賃物及租賃物上的附著物而無需補償就是天經地義的。為什么我們還要考慮土地使用權收回后的補償問題呢?筆者認為,我們之所以要在收回土地使用權時給受讓人以補償,是因為土地使用權的出讓在本質上是一種物權交易。雖然交易的客體是物的使用權,但在我國實行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的制度之下,使用權的出讓已經具有獨立性,因此這種交易行為設立的是一種物權關系而非債權關系。也正因為如此,土地出讓金必須一次性或短時間內分次交清,即使是最長的使用期限為70年的住宅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出讓金的交納也是如此,而不像租賃關系那樣通常按年度交納。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立法者以土地使用權出讓的租賃性質為支撐,實際建立的卻是一種物權關系,而在物權關系中又融入了債權的內容和表達方式,這可能正是我們在土地使用權期限屆滿時,對于是選擇物權化的處理方式還是選擇債權化的處理方式感到左右為難的真正原因。 (3)對于土地使用權期限屆滿后的處理,沒有考慮對以出讓和劃撥兩種不同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的產權人公平對待問題,因此有可能造成房屋產權領域的嚴重不公平。
我們知道,國有土地的供應主要采用無償(低償)劃撥和有償出讓兩種方式,前者沒有使用期限的限制。雖然從理論上說,以無償方式取得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國家可以隨時收回,但收回的前提必須是因為公共利益需要,而且在收回時必須給予土地使用人和房屋產權人以補償安置。同時,補償安置的原則之一就是,其新的安置用房或貨幣補償款所能購置的房屋的建設標準至少不低于被拆除的房屋。因此,劃撥土地使用權的無期限性不僅在事實上成為一種永久使用權(收回的同時還必須給使用人新的土地),而且地上房屋也具有永久產權,即使拆除也可以獲得充分補償。我國實行住房制度改革以后,人們通過“公房出售”方式購買的房屋或者經濟適用住房,其占用范圍的土地基本上都是劃撥土地。此外,在實行住房制度改革以前就早已大量存在的城市私房,其占用的土地也均無使用期限的限制。如果對其進行拆遷,即使這些房屋已經使用了幾十年、上百年,破敗不堪,殘值所剩無幾,也必須給予充分的安置補償。以上房屋產權人,無論其房屋是住宅還是非住宅,其被收回土地使用權和拆除房屋后不僅都能獲得高于原房屋建設標準的安置補償,而且根本無需再交納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可是采用有償出讓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的房屋產權人!不僅土地使用權有期限的限制。而且期滿后要么被無償收回,要么需補交出讓金,要么只能獲得相當于房屋殘值的補償。而對于能否續期、續期多久、交多少費用等問題,房屋的產權人基本沒有發言權。可是我們知道,以出讓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建成房屋并對外出售,其房價中所包含的土地成本大都在40%以上。為什么為土地支付了巨額對價的房屋產權人,對土地所享受的權益卻比以無償(低償)方式取得土地的房屋產權人要少,其土地被收回所享受的待遇要低得多呢?這種制度設計對以不同方式取得土地的房屋產權人采取不同對待的合理性是什么?用不了多久,成千上萬以出讓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的房屋產權人就會面臨土地使用期限屆滿的問題,到時候國家真的可以無償并且強制性地收回土地而無需對產權人給予安置補償或者讓產權周再次交納巨額土地出讓金才能允許其繼續使用土地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鐲為什么對劃撥土地的產權人不能采取同樣的對待呢?也許有人會說劃撥用地的使用目的是公益性質,而出讓用地是經營用地,兩者用途不同。但我們鈕道,在劃撥土地上建經營性項目的情形在全國并非個別現象,而出讓土地上的建設項目也并非全都毫無公益性。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對于土地使用期限屆滿后的處理問題,在現有的土地制度框架之下,我們確實難以設計一種既可以平衡各方面利益關系,又有充分法理基礎、周密可行的解決辦法。這不是學者和立法專家的無能,《物權法》僅僅做了有限的立法變化而將大部分問題繼續擱置,也實屬無奈。因為問題是由我國獨特的土地使用制度決定的,因制度本身先天缺陷而產生的問題,有時無論怎樣努力也是難以解決的。
因此,筆者認為,應當首先修改和完善我們現有的土地使用制度。既然土地使用權最高期限的規定本身就未加充分論證,缺乏合理性,那么就應當首先對此加以修改。規定土地使用權最高期限的是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對此加以修改可能比立法性修改程序要相對簡單一些。在對使用期限究竟規定多長才更加合理一時不能作出準確論證的情況下,筆者建議可參考土地承包經營權延包的方法,由國家根據土地的不同用途統一規定一個續期期限,除根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土地外,一律自動延長若干年限。其次,土地期限自動延長后,使用者無需再一次性交納巨額土地出讓金,可考慮參照征收房產稅的辦法,由土地使用者按年交納土地使用稅。這一稅種同樣只適用于經營性用房,對居住用房則不予征收。這種有所區別并且較輕的賦稅,不會增加產權人太重的負擔,即使其無力負擔,也可以通過出租、轉讓等方式轉移負擔。最后,無論是提前收回還是期限屆滿后收回土地使用權,國家必須給使用人以充分的補償和安置,而且安置補償的標準不應低于土地使用權收回前的房屋使用標準。同時,使用權收回時地上房屋等不動產的歸屬不能依照約定處理。因為在當今政府壟斷土地的一級出讓市場的情況下,土地出讓合同中的許多約定并不是平等協商的結果。為了獲得土地,受讓人除了全盤接受出讓人的合同條件外幾乎沒有其他選擇。如果按照土地出讓合同中的約定確定房屋的歸屬,那么其幾乎都要歸出讓方——政府所有。如此簡單處理不僅有失公平,而且會引發新的社會問題。到時候政府真可以依據當初的一紙出讓合同約定,強遷土地使用人而不用對其進行安置和補償嗎?何況關于期限屆滿地上物歸屬的約定均是土地使用權受讓方——開發商與政府土地管理部門簽訂的,而地上房屋建成后是由眾多獨立的小業主取得房屋產權。開發商當然知道自己不是未來建成房屋后的產權人,因此作出土地期限屆滿將房屋無償交還出讓人的承諾,這對他來說沒什么影響。可是他們的承諾能夠自動轉化為今后購房小業主的義務嗎?因此,《物權法》關于非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期限屆滿,地上房屋歸屬依約定處理的規定仍不盡合理,因為強調“依照約定”等于直接宣布歸政府所有。故關于土地使用期限屆滿地上房屋的歸屬在目前情況下不能依“約定”,而只能法定。由于現在法定的結果也是歸政府,因此毫無疑問,這樣的規定應當予以修改。其實歸政府所有也不是不可以,但政府有義務給原使用人以合理的安置和補償。
摘自:張慶華著《土地物權疑難法律問題解析(建筑房地產法實務指導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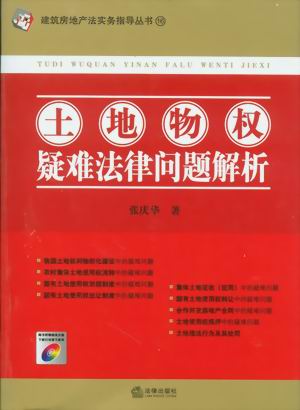 可以說,土地使用期限屆滿后土地使用權及地上物如何處置,一直是令立法者頭痛不已的難題。人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物權法》的制定上,然而《物權法》的規定看來仍不能讓人滿意。筆者認為,我們在立法時的思路選擇可能有問題,并對如下問題可能欠缺考慮: (1)當初《暫行條例》對不同用途的土地所規定的最高使用期限的依據是什么?比如,為什么住宅用地的最高期限是70年而不是50年或100年7汶一如此明確的量化標準是如何計算出來的?有何科學依據或法理依據?據說當初借鑒參考了香港的有關規定,可是中國大陸的土地制度和香港的土地制度有可比性嗎?如果這一期限的規定本身就缺乏合理依據,那么很可能這一規定本身就是錯誤的。就錯誤的問題怎么可能找出正確的答案和解決辦法呢? (2)當初立法者規定土地使用權的最高期限,其主要考慮的就是我國土地所有權不能買賣,能進行買賣和交易的只能是使用權,而土地使用權的交易是在所有權人保留所有權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這種交易具有明顯的租賃性質。既然土地使用權的出讓具有租賃性質,當然土地使用權作為出租物就不能沒有使用期限。 但是,如果強調土地使用權的租賃性質,則租賃期滿后所有人收回租賃物及租賃物上的附著物而無需補償就是天經地義的。為什么我們還要考慮土地使用權收回后的補償問題呢?筆者認為,我們之所以要在收回土地使用權時給受讓人以補償,是因為土地使用權的出讓在本質上是一種物權交易。雖然交易的客體是物的使用權,但在我國實行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的制度之下,使用權的出讓已經具有獨立性,因此這種交易行為設立的是一種物權關系而非債權關系。也正因為如此,土地出讓金必須一次性或短時間內分次交清,即使是最長的使用期限為70年的住宅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出讓金的交納也是如此,而不像租賃關系那樣通常按年度交納。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立法者以土地使用權出讓的租賃性質為支撐,實際建立的卻是一種物權關系,而在物權關系中又融入了債權的內容和表達方式,這可能正是我們在土地使用權期限屆滿時,對于是選擇物權化的處理方式還是選擇債權化的處理方式感到左右為難的真正原因。 (3)對于土地使用權期限屆滿后的處理,沒有考慮對以出讓和劃撥兩種不同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的產權人公平對待問題,因此有可能造成房屋產權領域的嚴重不公平。
可以說,土地使用期限屆滿后土地使用權及地上物如何處置,一直是令立法者頭痛不已的難題。人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物權法》的制定上,然而《物權法》的規定看來仍不能讓人滿意。筆者認為,我們在立法時的思路選擇可能有問題,并對如下問題可能欠缺考慮: (1)當初《暫行條例》對不同用途的土地所規定的最高使用期限的依據是什么?比如,為什么住宅用地的最高期限是70年而不是50年或100年7汶一如此明確的量化標準是如何計算出來的?有何科學依據或法理依據?據說當初借鑒參考了香港的有關規定,可是中國大陸的土地制度和香港的土地制度有可比性嗎?如果這一期限的規定本身就缺乏合理依據,那么很可能這一規定本身就是錯誤的。就錯誤的問題怎么可能找出正確的答案和解決辦法呢? (2)當初立法者規定土地使用權的最高期限,其主要考慮的就是我國土地所有權不能買賣,能進行買賣和交易的只能是使用權,而土地使用權的交易是在所有權人保留所有權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這種交易具有明顯的租賃性質。既然土地使用權的出讓具有租賃性質,當然土地使用權作為出租物就不能沒有使用期限。 但是,如果強調土地使用權的租賃性質,則租賃期滿后所有人收回租賃物及租賃物上的附著物而無需補償就是天經地義的。為什么我們還要考慮土地使用權收回后的補償問題呢?筆者認為,我們之所以要在收回土地使用權時給受讓人以補償,是因為土地使用權的出讓在本質上是一種物權交易。雖然交易的客體是物的使用權,但在我國實行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的制度之下,使用權的出讓已經具有獨立性,因此這種交易行為設立的是一種物權關系而非債權關系。也正因為如此,土地出讓金必須一次性或短時間內分次交清,即使是最長的使用期限為70年的住宅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出讓金的交納也是如此,而不像租賃關系那樣通常按年度交納。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立法者以土地使用權出讓的租賃性質為支撐,實際建立的卻是一種物權關系,而在物權關系中又融入了債權的內容和表達方式,這可能正是我們在土地使用權期限屆滿時,對于是選擇物權化的處理方式還是選擇債權化的處理方式感到左右為難的真正原因。 (3)對于土地使用權期限屆滿后的處理,沒有考慮對以出讓和劃撥兩種不同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的產權人公平對待問題,因此有可能造成房屋產權領域的嚴重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