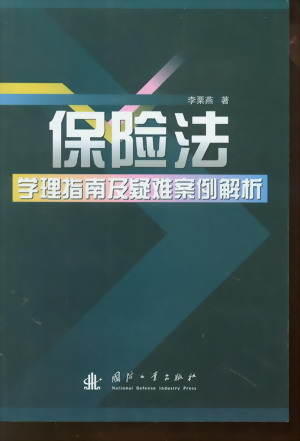
劉某與韓某原系夫妻,1999年二人因感情不合離婚,兒子劉星(現(xiàn)年7歲)由劉某撫養(yǎng)。2000年8月韓某在前夫劉某的勸說下為本人投保祥和定期保險,保額30萬元,受益人為其子劉星。2001年8月6日,劉某攜帶兇器到韓某住處將其殺害,并縱火焚尸以毀滅罪證,后被捕。在公安機關審訊中,劉某承認當初勸說韓某投保時就已萌生殺害韓某騙保的念頭。由于劉某喪失監(jiān)護資格,劉某在獄中通過公證方式將法定監(jiān)護人變更為劉某之母。2001年9月20日,受益人劉星的奶奶(變更后的法定監(jiān)護人)向保險公司提出索賠。
處理意見:有一種傾向性的意見認為此案應拒付,理由主要有以下三個。第一,劉某在勸說韓某投保之際,就有殺人騙保的念頭,而且他在供述中也承認殺人的動機是獲取保險金。可見,劉某為獲得這筆保險金蓄謀已久,具有道德風險。 第二,劉某雖然既非投保人,也非受益人,但是由于他是受益人的法定監(jiān)護人,因此對保險合同具有間接利害關系,是間接受益人,保險公司可以類推適用《保險法》第65條,不予承擔保險責任。 第三,劉某的罪行在當?shù)匾鸸珣崳税溉糍r付,將不利于伸張正義,有損保險公司的社會形象。 此種觀點是基于合同無效的前提而提出的,本案中韓某與保險公司簽訂的保險合同因違反社會公共利益而無效。既然合同自始無效,當然就不存在給付保險金一說了。解析 首先,我們要先明確何為人身保險合同,根據(jù)《保險法》第52條的規(guī)定,人身保險合同是指以人的壽命和身體為保險標的的保險合同。依照此規(guī)定,投保人向保險人支付保險費,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nèi)因保險事故遭受人身傷亡,或者在保險期屆滿時符合約定的給付保險金條件時,應當向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給付保險金。 第二,根據(jù)上面案例,我們了解到投保人韓某與保險公司簽訂的保險合同是出于自己的真實意思表示簽訂的有效合同,依據(jù)《民法通則》第55條規(guī)定,民事法律行為的一般生效要件是:①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②意思表示真實;③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在本案中,投保人韓某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有獨立簽訂保險合同的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當事人的主觀意思也并沒有違反社會公共利益,并且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實無瑕疵,雖然韓某是在丈夫劉某的勸說下投保的,但并不存在任何的威脅或者其他使投保人意思表示不真實的行為存在,因此不能將此合同視為自始無效。 第三,本案中的保險合同從訂立程序到合同內(nèi)容都遵循了最大誠實信用原則,不存在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的情況。犯罪嫌疑人劉某的行為雖然觸犯了《刑法》的有關規(guī)定,但這并不是投保人韓某的行為,并不能表明投保人韓某的行為違反了《保險法》的規(guī)定,劉某與韓某的行為之間并不存在聯(lián)系,因此劉某的行為不會對保險合同的效力有任何的影響。 第四,在處理意見的第一條中提到,此案中存在道德風險。要認清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先清楚地理解道德風險的含義。道德風險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為騙取保險金,采用欺詐、脅迫或惡意串通等不正當手段訂立保險合同,并存在故意制造保險事故的危險。本案中,投保人韓某的行為并不具有任何道德風險,有騙保和詐取保險金行為的主體是犯罪嫌疑人劉某,而劉某并不是保險合同的當事人,是保險合同關系外的第三人,因此此案不具有道德風險。 第五,處理意見的第二點提出了間接受益人的概念。《保險法》第65條規(guī)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傷殘或者疾病的,保險人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險費的,保險人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向其他享有權利的受益人退還保險單的現(xiàn)金價值。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或者傷殘的,或者故意殺害被保險人未遂的,喪失受益權。本案中受益人是韓某的兒子。首先被保險人指定了受益人,受益人不符合《保險法》第65條的規(guī)定,因此不能類推適用《保險法》的有關規(guī)定。同時“間接受益人”是個虛擬名詞,國內(nèi)外無論是保險法律還是保險理論都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間接受益人”的說法。另一種說法認為,雖然“間接受益人”的概念并不存在,但劉某間接受益的事實是存在的,受益人是一個年僅7歲的兒童,他是需要監(jiān)護人的,而投保人韓某死了,那么他的監(jiān)護人就必然是其父親劉某,如果不是因為劉某的犯罪行為被人發(fā)現(xiàn),那么受益人所領取的保險金必然由劉某代其保管,因此,劉某對這筆保險金是具有間接保險利益的,所以保險公司依據(jù)《保險法》第65條的規(guī)定將此作一個類推解釋作為拒賠的理由。此觀點的錯誤在于:第一,該觀點并沒有準確地把握受益人這個概念。所謂受益人,《保險法》第22條是這樣規(guī)定的: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險中由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險金請求權的人,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可以為受益人。可見,受益權的產(chǎn)生方式是投保人或被保險人的指定,受益權來源于被保險人的權利讓渡,其性質(zhì)是一種對保險金的所有權。本案中的受益人是劉星,即使是其父親劉某拿到這筆保險金也是代其兒子保管,他并不擁有保險金的所有權,因此犯罪嫌疑人劉某對這筆保險金不存在保險受益的關系。第二,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對監(jiān)護權的性質(zhì)缺乏足夠的認識。民法上,監(jiān)護權是對行為能力欠缺的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的合法權益實施管理和保護的法律資格,其本質(zhì)是民事代理權的一種。代理最主要的特征是代理人必須以被代理人的名義實施法律行為,且代理的效果直接歸屬于被代理人。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劉某的行為已經(jīng)導致他不具有對劉星的監(jiān)護權,也就無代理權;即使劉某沒有喪失監(jiān)護權,劉某也僅是有代理權,對保險金無權據(jù)為己有,也無權隨意支配。可見,保險公司的拒賠理由是不能夠成立的,而上述反對意見對所引用的《保險法》第65條有所爭議。因此,首先我們要認識到《保險法》第65條的不合理性表現(xiàn)在哪里。①倘若受益人為數(shù)人時,則只要其中一人有上述故意行為,保險公司就可以拒絕承擔保險責任,那么其他無辜受益人的期待權該如何保障?②若受益人有上述故意行為致使保險公司拒賠,則被保險人不但因受益人的行為使生命或身體受到侵害,而且喪失了獲得保險金的權利。由此可見,《保險法》第65條在自身的立法目的上與《保險法》的整體價值取向上是不一致的,與其他法條存在著很大的沖突,同時存在法律漏洞。本著公序良俗的原則,當受益人因故意制造保險事故而喪失受益權時,保險公司不能因此而免除應承擔的保險責任,仍應向其他受益人或被保險人的繼承人給付保險金。因此,以間接受益關系主張拒賠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第六,在第三種處理意見當中,一部分反對者認為,如果保險公司進行賠付,將不利于伸張正義,有損保險公司的社會形象。這顯然是一種錯誤的想法。在當今的社會中,人身保險發(fā)揮著它不可忽視的作用。人身保險事業(yè),使我們在生、老、病、死、殘時,能夠得到物質(zhì)上的幫助。它有利于深化改革和社會安定,也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設,能起一種“精巧的社會穩(wěn)定器”的作用。本案進行賠付正是保險公司重合同守信用的表現(xiàn)。一部分人將劉某的犯罪行為與保險合同這兩個事物混淆起來,并沒有真正地認清案件的實質(zhì)問題。持這種觀點的人只是看到了劉某的行為,并沒有考慮到受益人的利益。受益人僅是一個7歲的兒童,他的母親已經(jīng)死去,而父親又要在監(jiān)獄當中度過一生,他需要這筆保險金作為他以后的經(jīng)濟來源,如果不給付他保險金,他的生活將無所依靠,因此我們不能支持這種觀點。
摘自:李栗燕著《保險法學理指南及疑難案例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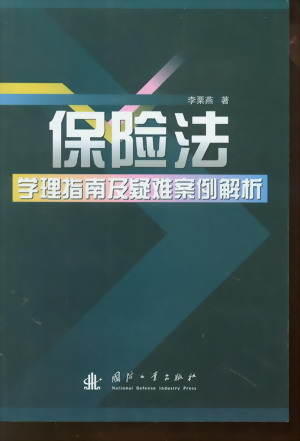 劉某與韓某原系夫妻,1999年二人因感情不合離婚,兒子劉星(現(xiàn)年7歲)由劉某撫養(yǎng)。2000年8月韓某在前夫劉某的勸說下為本人投保祥和定期保險,保額30萬元,受益人為其子劉星。2001年8月6日,劉某攜帶兇器到韓某住處將其殺害,并縱火焚尸以毀滅罪證,后被捕。在公安機關審訊中,劉某承認當初勸說韓某投保時就已萌生殺害韓某騙保的念頭。由于劉某喪失監(jiān)護資格,劉某在獄中通過公證方式將法定監(jiān)護人變更為劉某之母。2001年9月20日,受益人劉星的奶奶(變更后的法定監(jiān)護人)向保險公司提出索賠。
劉某與韓某原系夫妻,1999年二人因感情不合離婚,兒子劉星(現(xiàn)年7歲)由劉某撫養(yǎng)。2000年8月韓某在前夫劉某的勸說下為本人投保祥和定期保險,保額30萬元,受益人為其子劉星。2001年8月6日,劉某攜帶兇器到韓某住處將其殺害,并縱火焚尸以毀滅罪證,后被捕。在公安機關審訊中,劉某承認當初勸說韓某投保時就已萌生殺害韓某騙保的念頭。由于劉某喪失監(jiān)護資格,劉某在獄中通過公證方式將法定監(jiān)護人變更為劉某之母。2001年9月20日,受益人劉星的奶奶(變更后的法定監(jiān)護人)向保險公司提出索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