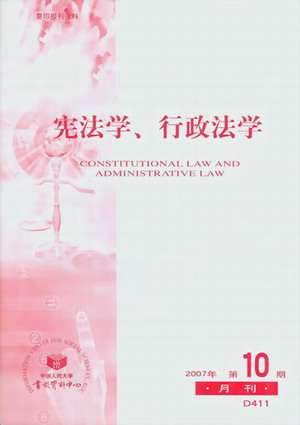
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引發的法學及媒體責任思考(上) 人大書報中心《憲法學.行政法學(2007年第10期)》
令人矚目的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①在各方的力促下以開發商和被拆遷人達成和解的形式落下了帷幕。在事件結束的第一時間,筆者即談到:“這可以說是一個把壞事變成好事的成功范例。此案最終沒有通過強拆的方式解決,說明在公權與私權背馳的情況下,重慶市方方面面始終采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顯示了政府對私有財產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說明重慶作為直轄市,在應對公共危機方面,比過去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物權法實施后,這類沖突還會更多,我們應從這個案例中總結經驗和教訓,同時應把調解這一傳統有效的糾紛解決方式繼續發揚,作為處理民事糾紛的最好手段來加以利用,以全面實現司法為民和司法和諧。”②事件過后,我們再心平氣和地、理性地反思該事件,從中確能感悟出許多…… 一、釘子戶事件的始與終
重慶釘子戶事件真正進入公眾的視野始于2007年3月初網上各大論壇流行的“史上最牛的釘子戶”的帖子。此后,通過記者的調查報道和渲染,釘子戶事件的全貌得以展現在人們面前。 事件所涉房屋地址為重慶楊家坪鶴興路17號。楊家坪鶴興路片區地處九龍坡區商業核心地段,緊鄰楊家坪步行商業區和輕軌楊家坪站,有住宅204戶、非住宅77戶。住宅戶全部為非成套住宅,無廚無廁,無天然氣和下排系統,其中有159戶面積不足35平方米,最小的不足8平方米。該片區80%的房屋系上世紀40、50年代前修建,多數為穿透夾墻等簡易結構建筑,年久失修,危舊破爛。經專業技術部門鑒定,72.2%的建筑系危房,并多次發生火災和垮塌事故,近10多年來被市、區兩級列為消防安全、房屋安全重點監控及整改片區,安全隱患極為嚴重。同時,該地段是連接步行商業區內外的重要通道,人、車流量較大,在未實施拆遷以前,人行道路狹窄且破損嚴重,最窄處不足1米,導致交通擁堵。廣大群眾急切盼望對該片區實施改造。市、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多次呼吁政府加大力度,為消除該片區安全隱患、確保人民群眾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提升楊家坪中心區域城市形象而早日對鶴興路進行徹底改造。 按照楊家坪步行商業區城市建設總體規劃,2004年,重慶智潤置業有限公司與重慶南隆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聯建的方式啟動了對該片區的改造,開發建設“正升一百老匯廣場”項目。該項目原國土批準用地面積為2.35萬余平方米,其中實施楊家坪環道、大件路、輕軌、公交換乘站等市政設施建設用地約1萬平方米,辦公、商用、住宅綜合建設用地為1.3萬余平方米。該項目建成后,對提升城市形象、完善城市功能、繁榮楊家坪商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004年8月31日,開發商取得拆遷許可證,啟動拆遷。此后經過開發商和被拆遷戶協商,至2006年8月,該片區281戶中有280戶接受了安置補償方案,同意拆遷。但17號房屋業主楊武與開發商雖經多次協商卻未能達成一致意見。2007年1月11日,開發商向重慶市九龍坡區房管局(以下簡稱房管局)申請行政裁決。當日,房管局即裁決被拆遷方在15日內自行搬遷并將房屋交由開發方拆除。但楊武并沒有按該裁決書履行義務,房管局遂于2007年2月1日向九龍坡區人民法院f以下簡稱法院)提交了《先予強制執行申請書》,申請法院強制拆遷。法院受理該申請,于3月19日舉行聽證會后作出《重慶市九龍坡區人民法院非訴行政執行裁定書》,裁定楊武在2007年3月22日前履行房管局裁決書第三項所確定的義務,即自行搬遷并將房屋交付拆遷人拆遷,逾期不履行法院將依法強制執行。但楊武并沒有履行該裁定,經法院多次組織協商仍未與開發商達成
協議。3月30日,法院發出執行公告:責令被執行人楊武在4月10日前自行搬遷,若到期仍不履行,法院將擇期依法實施強制拆除。③ 4月2日下午,在九龍坡區委負責人進行相應工作的前提下,開發商和被拆遷人楊武的代理人吳蘋在九龍坡法院的主持下,最終達成異地產權調換安置的和解協議:楊武位于鶴興路片區17號的房屋按照評估價價值為247萬余元,此外開發商還得補償楊武房屋裝修費10萬元、搬家費2萬元和屋內設備費2222元,總計近260萬元;由于開發商提供的位于沙坪壩區的異地安置房價值為306萬余元,故楊武需補足46萬余元的結構價差。同時,雙方還就因斷水斷電斷交通給楊武造成的營業損失達成了賠償協議,楊武獲得90萬元賠償。④協議達成的當天下午,楊武從開發商專門制作的梯子走下“孤島”,當天晚上10點36分“孤島”在機器的轟鳴聲中頹然倒塌,至此曠日持久的拆遷矛盾終于化解,備受關注的重慶釘子戶事件以和解的方式成功解決。 二、事件過程中的各方觀點
重慶“釘子戶”事件出現的大背景是:城市改造過程中,不少被拆遷戶對強制拆遷和安置補償不滿,強制拆遷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房地產價格持續大幅攀升,購房成為老百姓的痛苦負擔,人們對房地產商痛恨有加;《物權法》剛剛通過,作為維護民事主體權利的基本法律,社會各界對其學習研究正在進行中。在此種背景之下,該事件顯得格外引人注目,不僅引發了媒體和公眾的高度關注,也作為一個典型案例激發了法學家和其他專家學者的興趣,各種觀點、爭論、質疑爭鳴不斷,意見紛呈。 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朱巖認為,若《物權法》生效,“釘子戶”可勝訴;⑤江平教授認為,吳蘋以不涉及公共利益而拒絕搬遷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他說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了?!”如果補償合理就應該拆遷,要按照法院的裁定執行;⑥梁慧星研究員則采取了假設法而不是直接對該事件進行點評,即“如果你自己得到的利益很少,但大家的損失很大,尤其是開發商合法取得土地的使用權,他的權利也受損,就應該拆遷”;⑦孫憲忠教授則認為,強拆恐怕太草率,不能這么簡單化,強拆不會是一個光彩的記錄;⑧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孝正認為,可以讓這房子留著,建設一個公園,這是一個里程碑,它是一種精神財富,可以提高我國的國格;⑨社科院周大偉研究員認為,重慶的舊城改造從長遠來看,有利于老百姓的生活,城市化的理由也很正當,是一股不可阻攔的潮流,是符合公共利益的范疇;⑩中國政法大學王衛國教授認為:“征收、征用的主體是政府,拆遷是政府征收個人房屋所有權的行為,開發商沒有實施這種行為的資格。政府征收行為要具備法定條件,符合法定程序。在城市拆遷中,政府應該充分證明拆遷項目具備公共利益的目的,并經過城市規劃、人大審議、評估聽證、中介機構評估財產和與被拆遷人協商等一系列程序。如果政府和被拆遷戶因為拆遷發生爭議,應該由司法機關來裁判。”⑩西南政法大學趙中頡教授認為,國內某些媒體的錯誤解讀和誤導傳播,加之國外媒體的惡意渲染報道,更是將本事件賦予了某種特定的法學意義、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而網民和普通社會大眾則一邊倒“同情”拆遷戶,支持楊武夫婦抗爭到底。
三、事件引發的法學問題思考
網民和社會大眾一邊倒支持“釘子戶”、痛罵房地產商和政府的做法顯得偏激和情緒化,專家學者各執一詞的觀點也值得探討。筆者認為,本案不適用《物權法》,新通過的《物權法》要從2007年10月1日才開始施行,因此在物權法施行前,仍然應適用我國現有的有關房屋拆遷的法律法規。同時認為物權法實施后不達成協議就不能強制征收個人私有房產的說法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因為物權法第42條明確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對集體、私人的不動產進行征收,《物權法》并沒有對公共利益概念進行界定,也無法對本案所涉拆遷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進行判斷,在《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未被廢除之前,《物權法》的實施并不能否認拆遷的合法性;并且如果純粹認為物權法的規定是為了保護個人私有財產,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征收個人不動產,那將來城市改造就難以進行了,因此顯然是對物權法的一種誤讀。強制拆遷必須按照現行法律依法定程序進行,必須履行的程序包括:第一,拆遷人應依法取得拆遷許可證方能實施拆遷;第二,拆遷過程中,拆遷人應按規定與被拆遷人進行協商以達成拆遷協議;第三,在協商不一致的情況下,經拆遷當事人申請,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作出裁決,在裁決送達之日起3個月內雙方當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第四,如果被拆遷人在規定的期限內沒有履行搬遷義務就可以實施強拆,方式一是由房屋所在地政府責成有關部門直接進行,另一種是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當然,強制拆遷也不是最好的辦法,事件以和解的形式得以解決是最理想的結果。事件發展至此,矛盾已經得到解決,但是隱藏在矛盾背后的問題還值得我們思考。
(一)適用法律問題分析
依據《行政訴訟法》第66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88條的規定,在起訴期限屆滿前房管局不能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而根據行政法的基本原理和《城市房屋拆遷行政裁決工作規程》(以下簡稱《拆遷規程》)第17條的規定,以及《行政訴訟法》第44條和《行政復議法》第21條的立法精神,房管局可以在被拆遷人履行期限屆滿后起訴期限屆滿前申請法院強制執行。適用不同的法律得出了不同的結果,立法的矛盾使司法陷于尷尬中。 2001年國務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16條規定:“當事人對裁決不服的,可以自裁決書送達之日起3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拆遷人依照本條例規定已對被拆遷人給予貨幣補償或者提供拆遷安置用房、周轉用房的,訴訟期間不停止拆遷的執行。”據此,被拆遷人起訴的法定期限為3個月。本案中,房管局裁決被拆遷方在15日內自行搬遷并將房屋交由開發方拆除,被拆遷戶履行義務的法定期限為15日。《行政訴訟法》第66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體行政行為在法定期限內不提起訴訟又不履行的,行政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依法強制執行。”由此推導出的結論是:強制執行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行政相對人在法定期限內不提起訴訟,二是行政相對人在法定期間內不履行。如果行政相對人在法定期限內雖不履行但依法提起訴訟的,仍不能強制執行,而行政相對人是否提起訴訟在起訴期限屆滿前并不能確定。《解釋))1第86條規定:“行政機關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六十六條的規定申請執行其具體行政行為,應當具備以下條件……(六)申請人在法定期限內提出申請……”以上的兩個“法定期限”到底是指3個月的起訴期限還是指15天的履行期限并不明確。《解釋》第88條規定:“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其具體行政行為,應當自被執行人的法定起訴期限屆滿之日起180日內提出。”據此,“法定期限”應指三個月的起訴期限。本案中,房管局是2007年1月11日作出、2007年1月16日向被拆遷人送達裁決書的,被拆遷人的起訴期限應于2007年4月15日屆滿,在期限屆滿前房管局不能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人民法院也不應受理強制執行申請。即使是訴訟期間強制拆遷的執行也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即已對被拆遷人給予貨幣補償或者提供拆遷安置用房、周轉用房的前提下才能進行強制拆遷。
根據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行政行為具有先定力和執行力,一經作出即具有效力,可以強制執行。《拆遷規程》第17條規定:“被拆遷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決規定的搬遷期限內未搬遷的,由市、縣人民政府責成有關行政部門強制拆遷,或者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拆遷。”只要被拆遷人在裁決規定的搬遷期限即履行期限內沒有履行義務的,即可強制執行。《行政訴訟法》第44條和《行政復議法》第21條規定了“訴訟期間和行政復議期間不停止具體行政行為的執行”的原則。根據以上分析,房管局可以申請強制執行,即使是訴訟或復議期間,裁決書的強制執行也可以不停止。 法院受理一般意義的強制執行申請形式上是有根據的,然而本案中,房管局向法院提出的是《先予強制執行申請書》,“先予執行”是否意味著具體行政行為尚未生效,如果裁決已生效為何還需“先予執行”而不“強制執行”?這顯然是一個難以解釋的矛盾問題。筆者認為,非訴具體行政行為不存在先予執行的問題,因為只有生效的具體行政行為才可申請執行,因此種執行就是一般的強制執行,不是先予執行。法院依據《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1第94條“被告或者具體行政行為確定的權利人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被訴具體行政行為,人民法院不予執行,但不及時執行可能給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先予執行”的規定作出先予執行的裁定顯然是存在問題的,因為該規定中先予執行的前提是“在訴訟中”,而本案尚未進入訴訟程序。 退一步講,即使是對已經提起訴訟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先予執行,其適用條件也非常嚴格。除先述先予執行的前提是“在訴訟過程中”,只有不先予執行會給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的情況下才適用先予執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曹建明曾在2004年12月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明確表示:“法院不得以任何形式參與拆遷,原則上不允許先予執行。”后來有人提問:“這個講話是曹副院長的個人意見還是最高法的態度?”曹建明斬釘截鐵地回答,這是最高法對此類案件的明確態度。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非訴行政執行工作的若干意見》第39條第2款也規定:“對涉及農村征地拆遷、城鎮房屋拆遷的具體行政行為不得裁定先予執行。”雖然后來重慶市高院又制定了《關于適用(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非訴行政執行工作的若干意見)第三十九條有關問題的通知》對上述規定作了修正,但修正后“通知”只規定:在可能會給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的情況下才可先予執行。而本案中很難說不先予執行會給國家、公共利益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16條規定:“拆遷人依照本條例規定已對被拆遷人給予貨幣補償或者提供拆遷安置用房、周轉用房的,訴訟期間不停止拆遷的執行。”據此,在沒有對被拆遷人予以安置之前不能強制執行,更遑論先予執行了。
筆者認為,當前我國法院不宜受理房管局在起訴期間屆滿前的強制拆遷申請。首先,《行政訴訟法》和《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是上位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屬于有權解釋,其適用的法律效力應優先于作為行政規章的《拆遷規程》。其次,起訴期間屆滿前法院受理并實施強制拆除(事實上是先予執行)將使被拆遷人在訴訟中處于被動地位。房管局在被拆遷人法定起訴期限屆滿前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法院受理并作出支持房管局裁決的裁定實際上剝奪了被拆遷人尋求司法救濟的權利。法院已經認定房管局拆遷行政裁決書“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合法,無超越職權和濫用職權”,當事人再起訴還有意義嗎?但是行政行為具有追求公益的目的,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必須賦予行政行為先定力和執行力,即若被拆遷人在法定期間內不履行義務可能損害公共利益的,在房管局的裁決書送達當事人未滿三個月前,行政機關可以按《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17條“被拆遷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決規定的搬遷期限內未搬遷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縣人民政府責成有關部門強制拆遷”的規定自行實行強制拆遷,但為避免法院的提前介入影響被拆遷人訴訟的積極性和對法院裁決的公正性,法院不宜受理強制拆遷申請。
摘自:人大書報中心《憲法學.行政法學(2007年第1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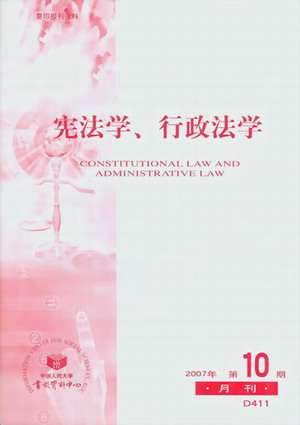 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引發的法學及媒體責任思考(上) 人大書報中心《憲法學.行政法學(2007年第10期)》
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引發的法學及媒體責任思考(上) 人大書報中心《憲法學.行政法學(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