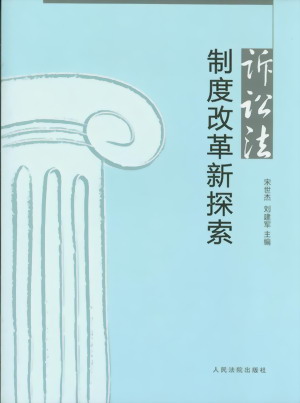
試論刑事訴訟中的證言拒絕權--《訴訟法制度改革新探索》
證人作證是維系刑事司法正常運轉的關鍵之所在,為使證人履行作證的義務,許多國家在立法中都明確規定了強制證人作證制度,與此同時,也都賦予了特定主體證言拒絕權。特定主體的證言拒絕權不僅為現代西方各國奉為通例,在我國也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我國臺灣地區就規定了特定主體的證言拒絕權。加強對刑事訴訟中證言拒絕權的研究,對完善我國證人作證制度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西方國家,證言拒絕權的確立由來已久,最早的證據拒絕權源于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親屬容隱”。目前,在英美等國,拒證規則被稱為特權規則,英國的證據法指出,特權是指即使證人具備適格性并且能被強迫作證,仍能以某種理由為依據拒絕答復某種問題。證據法上的特權規則將產生下述結果:在某些情形下,有關聯性的并且能證明的事實,不允許當事人予以證明;特權屬于某一個具體的人,當事人對特權所掩蓋的事實,仍能以其他證據加以證明。①現代各國雖然在法律傳統、社會觀念和訴訟結構上存在著差異,但是大多數國家確立了證言拒絕權。一般而言,享有證言拒絕權的主體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親屬拒證權
這在德國、美國、日本等國都有明確的規定。在大陸法系國家,如《德國刑事訴訟法》第52條規定:“……1.被指控人的訂婚人;2.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關系已不再存在;3.與被指控人現在或者曾經是直系親屬或者直系姻親,現在或者曾經在旁系三親等內有血緣關系或者在二親等內有姻親關系的人員都有權拒絕作證……”②上述人員可以放棄該權利,但是在詢問過程中可以撤回對該權利的舍棄。依據《意大利刑事訴訟法》第199條的規定:“被告人的近親屬沒有義務作證……”①在英美法系國家,依據《美國1999年統一證據規則》第504條的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配偶享有拒絕作出對被指控的配偶不利的證言的特免權。②在日本,根據《日本刑事訴訟法》第147條的規定:“任何人,都可以拒絕提供有可能使自己的配偶、三代以內的血親或二代以內的姻親,或者曾與自己有此等親屬關系的人受到刑事追訴或者受到有罪判決的證言。”⑧
(二)拒絕自證其罪的權利
拒絕自證其罪的權利是指由于陳述證言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追究或受到財產損失時可以拒絕作證。拒絕自證其罪來源于“任何人無義務控告自己”的古老格言。拒絕自證其罪原則的確立與否,反映了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入、被告人的人權保障程度。因此,西方國家在立法上普遍賦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絕自證其罪的權利。《英國法官規則》第2條和第3條規定訊問和提訊犯罪嫌疑人前應當告知“除非你自己愿意,否則你可不必作任何陳述,但是你一旦有所陳述,便將錄為證據之用。” 《法國刑事訴訟法》第116條規定:“……預審法官應通知受審查人有權保持沉默或者做出聲明或者接受詢問……”④《意大利刑事訴訟法》第64條第2款規定:“不得使用足以影響被訊問者同意能力或者改變其記憶和評價事實的能力的方法或技術進行訊問,即使被訊問者表示同意。”第3款規定:“在開始訊問前除第66條第1款的規定外,還應當告知被訊問者,他有權不回答提問,并且即使他不回答提問訴訟也將繼續進行。”⑤拒絕自證其罪的特權在有些國家還上升為憲法權利,如《美國憲法修正案》第5條規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
(三)職業秘密的證言拒絕權
職業秘密的證言拒絕權是指從事特定職業的人員對其在履行職責過程中所獲得的職業秘密有拒絕作證的權利。職業秘密的證言拒絕權的主體范圍比較廣泛,各國的具體規定也有所不同。大陸法系國家,如德國的職業特權主體就包括神職人員、辯護人、律師、專利代理人、財會師、宣過誓的查賬員、稅務顧問和稅務全權代表、醫生、牙醫、藥劑師、助產士、行使職務的咨詢人員、職務助理人員、法官、公務員以及期刊或無線廣播的準備、制作或發行人員等近20種。①根據《意大利刑事訴訟法》第200條規定:“律師、法律代理人、技術顧問、公證人、醫生等有權保守職業秘密。”②英美法系國家,如依據《美國1999年統一證據規則》第5條規定:“律師、精神病醫生、神職人員享有特權。”英國職業特權的主體有著嚴格限制,只承認法律職業特權,對于牧師、醫生等職業的證言拒絕權卻不予認可。英國大法官丹寧勛爵指出:“據我所知,只有一種職業有可以不向法院提供消息來源的特權,這就是律師職業。但這也不是律師的特權,而是他的委托人的特權。就拿牧師、銀行家或醫生來說,他們都無權拒絕回答法官提出的問題。”③此外,《日本刑事訴訟法》第149條規定:“醫師、牙科醫師、助產士、護士、律師(包括外國法事務律師)、代辦人、公證人、宗教職業者或者擔任過以上職務的人,對由于受業務上委托而得知的有關他人秘密的事實,可以拒絕提供證言。但本人已經承諾時或拒絕證言可以認為只是為了被告人的利益而濫用權利時(被告人為本人時除外),以及具有法院規則中所規定的其他事由時,不在此限。”④
(四)公務秘密的證言拒絕權
公務秘密的證言拒絕權,是指公職人員對涉及公務秘密的問題有拒絕作證的權利,法官和陪審官對案件的評議也屬于公務秘密。日本、英國、聯邦德國、美國等國均確立了公務秘密的證言拒絕權。依據《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605條和第606條的規定:“主持審判的法官不能在該審判中充當證人提供證詞,陪審團成員不能在自己充當陪審的案件中作為證人提供證詞。如果陪審員被傳喚作證,對方當事人有權被授予機會在陪審團不出席的情況下提出異議。”⑤英國確立了以公共政策為依據的證言拒絕權,該特權主要表現在與國家安全以及其他涉及國家的事項、偵查犯罪行為有關的官員可以拒絕作證,此外,也不能夠強迫法官就其在審理過程中所獲知的案件事實作證。《日本刑事訴訟法》第144條規定:“對公務員或者曾任公務員的人得知的事實,本人或者該管公務機關聲明是有關職務秘密的事項時,非經該管監督官廳的承諾,不得作為證人進行詢問。”⑥ 在我國,證言拒絕權最早可以溯源至西周時期的“親親相隱”。“親親相隱”與現代的證言拒絕權在內在價值機理方面存在明顯差異。“親親相隱”是以維護封建的倫理秩序為出發點,它不是被界定為“權利”,而是“義務”。如果違反了“親親相隱”的規定,則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唐、宋、元、明、清的法律甚至明文規定,根據法律應當相隱的親屬都不得令其作證,官吏如有違反要處杖刑。但是,“親親相隱”制度實施的效果與證言拒絕權有其類似之處,即近親屬不必承擔作證的義務。近代以來的多次立法如《大清新刑律》和“中華民國刑法”都明確賦予了近親屬之間的證言拒絕權,秉承了我國“親親相隱”的傳統。目前,我國臺灣地區仍然承認特定主體享有證言拒絕權。
新中國成立之后,在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問題上,更為注重有效地懲罰犯罪;在追求實體真實還是客觀真實的問題上,更為重視案件的實體真實,主張“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在這樣的法制背景下,揭發犯罪被認為是公民對國家所應當承擔的基本義務,因此,特定主體的證言拒絕權未被法律所確認。隨著我國法治化進程的深入,人們越來越重視自身權利的維護,從該角度而言,“中國社會進步的過程,就是公民權利得到切實保障和全面實現的過程,就是人的主體意識得到充分實現的過程。”①人們已由過去的注重懲罰犯罪,偏重社會的整體利益,轉向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相協調的方向發展。與此相適應,特定主體的證言拒絕權也逐漸獲得了人們的關注。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作證是證人對國家承擔的基本義務。筆者以為,明確證人有作證的義務是維護刑事司法正常運轉的關鍵之所在,如果否認證人的作證義務,在某種程度上會妨礙整個刑事司法的有效運轉。然而,在刑事訴訟中過于強調證人的作證義務在特定情形下不可避免地會造成一定的不利影響。以辯護律師為例,辯護律師揭發被追訴人所隱瞞的罪行,固然有助于在個案中實現公正,有效懲罰犯罪。然而,如果律師未能保守職業秘密,反而成為了追訴的工具,其直接后果就是被追訴人與辯護律師之間的信任關系消失于無形,甚至辯護律師自身的存在價值都會令人懷疑。因此,此時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是,當案件事實的查明妨礙或者影響了其他特定的社會利益時,如何進行價值選擇?筆者以為在明確證人有作證義務的同時,也應賦予特定主體證言拒絕權,從而為解決上述“選擇困境”提供出路。
此外,我國庭審方式的轉變為證言拒絕權的確立提出了制度要求。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正之后,確立了新的庭審方式。新庭審方式以控辯對抗、審判中立為其基本表征,以庭審的實質化為基本內容。為保障庭審實質化的實現,取消了審前的證據移送,取而代之的是“復印件主義”。然而,審前證據移送的取消并未實現理想中的庭審實質化。究其原因,并非在于試圖消除法官庭前預斷的立法初衷存在不妥之處,而在于相關的配套制度未能確立,尤其是在《刑事訴訟法》中雖然明確規定了證人有義務出庭作證,但是我國刑事訴訟中最為薄弱的環節仍然是證人出庭率不高。在我國目前的司法環境下,辯方的調查取證權受到限制,因此,對控方證據的有效性進行質證無疑是辯方的最佳辯護策略。證人出庭率不高所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法院的庭審難以實質化,庭審過程中辯方無法有效對控方收集與提供的證人證言進行質證,法庭不得不主要依賴于控方所提供的書面證言。庭審的“虛置化”無疑是我國目前刑事訴訟中出現錯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有效的保證我國證人出庭作證是學界探討的熱點問題,有學者提出了應確立強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強制證人出庭作證不失為解決我國證人出庭難的有效路徑,而且也是世界各國通行的做法。然而,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凡是知道案件真實情況的人都應當出庭作證。換言之,所有具有作證能力的人都應當作證,這種過于絕對的要求未考慮到證人作證的復雜性及其可能造成的相關社會影響,反過來影響了強制證人作證的實效。通過規定特定主體的證人有證言拒絕權,則對于有義務作證的證人的范圍可以具體化,使司法機關能夠明確應當作證的證人范圍,從而使強制證人作證能夠正當化,減少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如前所述,刑事訴訟中證言拒絕權的確立有其內在的必然性。鑒于賦予特定主體以證言拒絕權可能會對司法機關查明案件事實造成不利影響,筆者認為應當限制其主體范圍,具體而言應賦予以下三類主體證言拒絕權。 1·應確立近親屬的證言拒絕權:近親屬之間的相互信任是人類感情聯系的基礎,如果不賦予近親屬證言拒絕權,而強制要求指控其近親屬,則不利于家庭內部的和諧,而且該證言的證明力也往往令人懷疑。這是由于家庭成員之間往往是不計較利益得失的,為了維護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不顧事實的為其開脫的可能性更大。當然也不能排除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大義滅親”,然而這畢竟是少數人的行為,無法“放之四海而皆準”。因此,應確立近親屬的證言拒絕權,其范圍主要包括:配偶、父母和子女。 2·應確立律師的拒證權:律師以維護當事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合法權益為其基本職責,律師和當事人之間互信關系的確立是其有效履行職責的前提。對由于職業而獲悉的當事人秘密或個人隱私律師應當保密。律師保守職業秘密對當事人而言是其所承擔的義務,而對偵控機關而言則是律師享有的權利。我國《律師法》雖然規定了律師有保守職業秘密的義務,但是并未賦予律師相應的拒絕作證權。為保障律師能夠獨立的執業,有效維護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確立律師的證言拒絕權是有必要的。 3.應確立被追訴人拒絕自證其罪的權利:我國目前并未確立被追訴人拒絕自證其罪的權利,長期以來的刑事司法政策即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但是對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從該條的規定來看,盡管也賦予了“對于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權拒絕回答”的權利,但是在司法實踐中訊問的主動權由偵查人員掌控,因此,該權利往往形同虛設,“如實陳述”成為被追訴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基本義務。因此,筆者以為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應確立被追訴人拒絕自證其罪的權利,這盡管會使我國傳統的“由供到證”型的偵查模式受到沖擊,對有效懲罰犯罪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其所起到的正面作用遠大于其負面影響,不僅體現了對被追訴人權利保障的應有關注,而且有助于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為使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能夠兼顧,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得以平衡,我國的證言拒絕權也應設置例外。筆者以為應確立重大犯罪預謀的例外,即對于重大犯罪的預謀,公民都有義務予以揭示,以最大限度地遏制犯罪所帶來的危害。此外,為了有效保障特定主體的證言拒絕權,偵控機關詢問享有證言拒絕權的主體時,應履行告知義務,即詢問前應告知被追訴人、近親屬以及律師有拒絕作證的權利,否則偵控機關獲得的證言不具有法律效力。由于證言拒絕權從其本質上而言,是賦予特定主體的權利,因此,如果享有證言拒絕權的主體愿意提供證言,也可以提供。
摘自:宋世杰等主編《訴訟法制度改革新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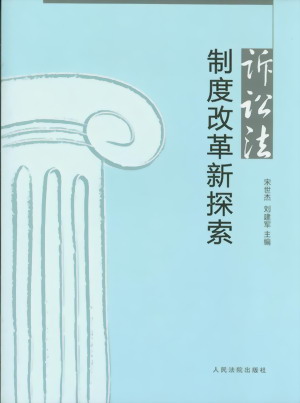 試論刑事訴訟中的證言拒絕權--《訴訟法制度改革新探索》
試論刑事訴訟中的證言拒絕權--《訴訟法制度改革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