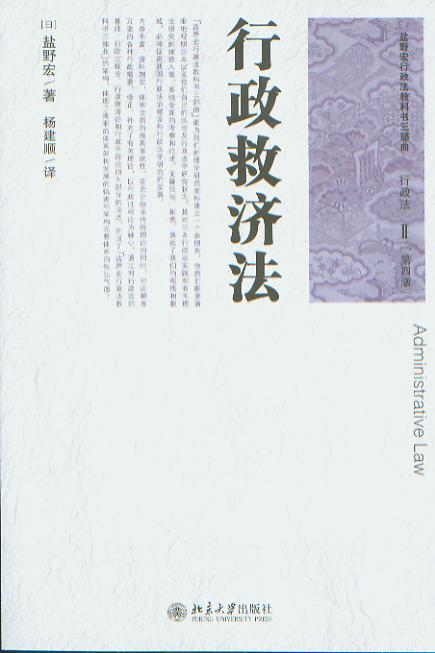
行政救濟論之國家補償的缺陷
一、問題狀況
在日本,國家賠償和損失補償,分別是作為不同的制度展開的。但是,從理論上看,存在著難以劃分為國家賠償和損失補償的任何一種的、所謂境界領域,如計劃變更①,事情判決(特別情況下的駁回判決)②,事業損失③等。進而,從國家補償制度全體來看,有人指出,存在著以迄今為止的國家賠償和損失補償這兩種制度無法包容的、國家補償不及的領域。④這里存在著如下范疇:
(一)屬于公權力的行使的公務員的行為雖然違法但是無過失的情況。《國家賠償法》第1條至少在修辭上是以存在公務員的過失為要件的。與此相對,人們雖然展開了過失概念本身的客觀化這種實體法上的對策以及過失推定等所謂程序上的對策,但是,那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按照以前的觀念的話,損失補償僅限定于合法行為。所以,雖然違法但是無過失的情況下,則不能依據國家賠償和損失補償的任何一種途徑得到救濟。
(二)營造物的設置、管理沒有瑕疵的情況。在《國家賠償法》第2條的解釋上,國家雖然承擔無過失責任,但是,并不是無瑕疵的情況下也承擔責任,即不是只要發生了危害,就必須對其結果承擔責任,這是通說性見解。我認為,無論在前后文邏輯性上,還是在沿革上,該見解都是適當的。對此,在現行制度下也存在救濟之手不能涉及的領域。
(三)進行強制性國家活動本身是法所承認的,但是,如果對因此而產生的損害置之不理,有時會產生違反正義的狀況。例如,在強制預防接種時,盡管是根據法的規定,并且也沒有怠慢于注意義務,但是,還是出現了后遺癥,有時甚至出現死亡的事例。在通常的損失補償中,對相對人帶來損失是法所承認的。與此相對,預防接種的后遺癥的發生并不是法從正面承認的,而觀其結果,卻產生了嚴重違反正義的狀況。盡管如此,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在國家賠償、國家補償的哪一種制度中,若以其傳統的形態來把握,則均是無法救濟的。
(四)公務災害、戰爭災害,是鑒于個人被置于危險狀況的損害,和(三)的范疇相類似,所以,有時將雙方一同作為危險責任來說明。但是,我認為,這種情況不是像預防接種那樣的個別的侵害行為,而是受害者被置于總括性環境存在危險,在這一點上可以與(三)的范疇區別開來。這些災害,以傳統的救濟方法也得不到全面解決,這是不言而喻的。
關于以上的國家補償不及的領域,從受害者方面來看,可以說是當然應該予以救濟的。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其救濟的費用最終只能由稅金來解決,在這種意義上,存在著解釋論的界限。即這里存在著如下問題:論及稅金的使用方法,那不是法官的工作(裁判),而是立法者的作用。
二、對應的狀況
(一)違法、無過失的情況
在公權力的行使違法、無過失的情況下,現行法上,進行了過失的客觀化、過失的推定等所謂對癥下藥療法。
但是,超過此范圍,既然現行法上明確規定以過失為要件,一般地說,要從正面否定過失的概念,作為解釋論是有困難的。因此,人們期待著個別的對策。作為制定法也并不是沒有對應事例。
例如,在《國稅征收法》的滯納處分程序中,當動產的出賣決定違法時,對善意的購買者不能要求返還,同時,國家此時被規定為承擔無過失的損害賠償的責任(第112條)。此外,《消防法》在對消防長、消防署長(市町村的機關)賦予防火對象物改善命令等權限時規定,當通過該命令的撤銷訴訟作出撤銷判決時,對因該命令所產生的損失,應當以時價予以補償(第5條、第5條之二、第6條)。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這些并不是一般性無過失損害賠償制度的前奏,而是分別由其各自固有的立法理由所支持的。就《國稅征收法》而言,國家設定國稅征收制度,其目的之一是確保國稅征收的順利運作,從調整購買人和舊所有者的利益的角度出發,結果由國家來補救相關損害。與此相對,在《消防法》之下,在緊急的情況下姑且承認發布命令,即在預測到違法行為之發生的基礎上,由該市町村無過失地承擔此時的損害。
問題不在于這里所說的個別對應,而在于對國家的行為是否應該從正面承認無過失責任這一點上。這關系到《國家賠償法》的根本性修改,因而成為將來的課題。①
(二)設置、管理無瑕疵的情況
關于營造物的設置、管理,不考慮瑕疵的存在而承擔責任這種意義上的結果責任,在解釋論上,不是通說和判例所采用的觀點。②此外,在立法論上也存在著無條件地全額以稅金來負擔因營造物而產生的損害是否適當的問題。在這里,應該采取包括有關水害、道路災害等的保險制度在內的災害防止及危險負擔的合理的、綜合的對策。
(三)關于正當行為的結果責任
雖然說行為本身是正當的,但是,有時作為該行為的結果卻使私人方面產生意想不到的損失。法律上雖然有對此作出規定的事例,但是,也存在需要通過解釋論來解決的問題。
1.作為法律上規定了補救的事例,《文化財產保護法》對在規定的修理(第38條)時受到損失者,規定由國家補償通常會產生的損失(第41條)。此外,對重要文化財產的所有者,文化廳長官為了提供于公開之用,可以發布參展命令(第48條)。對起因于參展的滅失、毀損,規定了相同宗旨的補償(第52條)。關于這種情況下的“損失補償”的性質,《文化財產保護法》沒有作出特別的規定。即,只要產生了損害,國家的行為便是違法的。故此,這里的補償,是應該視為無過失損害賠償呢?還是應該著眼于行為本身,只要沒有瑕疵,就是基于合法行為的,所以應該視為屬于損失補償的系列呢?僅依據法律條文,是不明確的。不過,在這種情況下,立法時并不一定有拘泥于損害賠償或者損失補償的理由,因而,只要作為文化財產的修繕、陳列這一公益目的和私人的財產權的保護的調整性立法,承認其合理性便足夠了。并且,這樣一來,將不以行為的違法、合法為問題的立法,作為承認了結果責任的立法來處理,也是可能的了。
2.就因預防接種所發生的事故而言,現在已經建立起了不管過失如何,進行一定的給付的制度(《預防接種法》,第16條以下)。但是,在該法制定以前也曾發生過預防接種事故,出現了過失的認定存在困難,救濟受阻的狀況。并且,在該法制定之后,也存在著給付額是否過低的問題。因此,人們展開了對其救濟能否通過損失補償法理來進行的討論。
其一是考慮到憲法第29條第3款的援用。關于預防接種事故的救濟,依據憲法第29條第3款來進行,則存在著該條款本來是以財產權為對象的之疑問。但是,在日本,損失補償的法理本身,是明治憲法以來,以公平負擔、特別損失的觀念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此時,作為觀念中的重要的適用例,的確一直是財產權。但是,那并不是概念的必要性前提條件。從以特別損失為核心的損失補償制度來看,憲法第29條第3款是承認了公平負擔、特別損失的財產情形之適用的,或者說僅此而已。這樣一來,關于因強制性預防接種而對某人產生的事故的救濟方法,采取對在《日本國憲法》下比財產具有更高的保護價值的生命、身體的合法侵害的損失補償的構成,作為其請求權的具體化,援用憲法第29條第3款,我認為是較實際的解釋。這種援用,是類推還是當然,并非本質上的差異。此外,援用憲法第29條第3款,并不等于從正面承認了對生命的剝奪和對身體的侵害。這是因為,援用的對象是對特別損失,基于公平負擔的見解的補償,而不是有意識的侵害行為。
雖然也可以發現有與這種觀點相對應的裁判例②,但是,損失補償說其后并未成為法院所采用的觀點,對于預防接種事故的現實的救濟,在日本,是通過認定預防接種之際的公務員的過失這種國家賠償法理來進行的。例如,東京高等法院平成4年12月18日判決③就采取了這種法理。該判決認為:“從與生命、健康的侵害這種重大的法益侵害相對比來看,不能說以成本及人手的問題為理由,可以使厚生大臣(當時)所采取的行動得以正當化”,在此基礎上,指出:“作為厚生大臣沒有采取為了識別……禁忌的充分的措施之結果,現場的接種擔當者錯誤地進行禁忌識別,對屬于禁忌者予以接種,應當說,是能夠預見像本案件中各事故那樣重大的副反應事故發生的。并且,……由于本案件中受害兒童們全部被推定為屬于禁忌者,所以,應當說,假設厚生大臣采取了識別禁忌的充分的措施,其結果,接種擔當者沒有錯誤地進行禁忌識別,將屬于禁忌者全部從接種對象者之中排除出去的話,本案件副反應事故的發生是可以規避的。所以,可以說,本案件副反應事故這種結果規避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作為結論,該判決指出:“不得不說,厚生大臣存在過失,即怠慢于采取為了避免對屬于禁忌者實施預防接種的充分的措施”。①該判決中有法院自身援用的兩個最高法院判決——后遺殘疾發生的情況下,屬于禁忌者的推定發揮作用的判決②,以及對擔當醫師賦課進行區別禁忌者提問這種高度的注意義務的判決——可以說,使得預防接種不是通過損失補償,而是通過國家賠償來進行救濟這種判例法理得以鞏固。
(四)有關危險狀態的責任
在承認國家補償的立法事例中,有的承認了對因國家設定危險狀態,或者將人置于危險狀態而發生的損害予以補償。例如,《國家公務員災害補償法》、《關于對警察官的職務協力援助者的災害給付的法律》、《關于基于在日本國滯留的美利堅合眾國軍隊等行為的特別損失之補償的法律》等。
預防接種事故補償、文化財產損傷補償,基本上也是以危險責任為根據的。但是,這其中也存在個別的公權力的行使和對其服從的關系,是規定對在該過程中所產生損失予以補救的。與此相對,這里考察的是,國家方面沒有個別的命令行為,而是國家創造出更加廣泛的危險狀態的情況下的損害的補救問題。
不過,僅被置于危險狀態,便一般地構成補償請求權,這是有困難的。即,危險狀態越是一般性的,補償的問題就越難以作出單義性的規定,與此相適應,是否應該補償的判斷權者,也從司法權之手轉移到立法權之手。戰爭災害就是其中的一種。對此,如果著眼于具體的每個人,雖然所蒙受的損害有輕重之分,但是,從司法上來辨別特別損失和非特別損失,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并且,如何補救該災害,可以說也是極其適合于立法性、行政性判斷的。①關于這個問題,最高法院昭和43年11月27日大法庭判決②認為,一般地說,戰爭損害是國民均應忍受的。進而,西伯利亞扣留請求案件③、在日韓國人的軍人、軍屬的年金恩給請求案件④、Bc級戰犯案件⑤等,對于這些與戰爭有關但與一般日本國民不同的情況,均承認了立法裁量,排斥了原告的主張。⑥
此外,即使立法上承認了對基于危險狀況在現實中發生的損失予以補救的情況,但是,正像有時同時具有國家補償的性質和社會保障的性質那樣,也會產生其性質不能作單義性區分的情況。最高法院在適用《關于原子彈受害者的醫療等的法律》之際,認為不需要居住關系。其論據是,該法具有作為社會保障法的性質,同時具有國家補償法的性質。
摘自:鹽野宏著《行政法Ⅱ(第四版)行政救濟法(鹽野宏行政法教科書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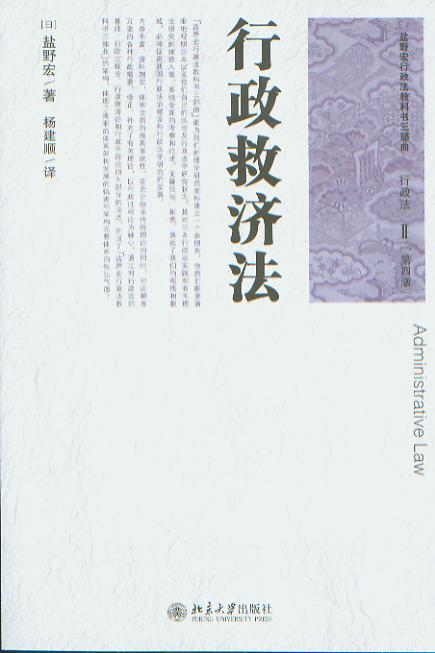 行政救濟論之國家補償的缺陷
行政救濟論之國家補償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