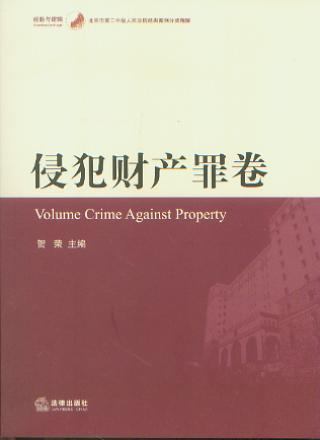
李振有等人盜竊案
依據:(2006)二中刑終字第930號刑事裁定書
核心法律問題:盜竊罪與職務侵占罪的區別。
案情介紹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董樹平、高紅超、趙艷春伙同被告人李振有經預謀后,于2005年11月8日1時許,在本市朝陽區姚家園東方基業汽車城“北京聯拓奧通汽車貿易有限責任公司奧迪4S店”內利用值班之機將該店的一輛“紅旗名仕”轎車及客戶魯鳳文停放在店內修理的一輛“奧迪A4”轎車、兩臺“IBM”電腦、二臺健伍牌對講機、一件西服(以上物品共價值人民幣474 900元)盜走。
二、法院判決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認為,被告人被告人董樹平、高紅超、趙艷春、李振有的行為構成盜竊罪。判決:(1)被告人董樹平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罰金人民幣一萬一千元。(2)被告人高紅超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罰金人民幣一萬一千元。(3)被告人趙艷春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罰金人民幣一萬一千元。(4)被告人李振有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罰金人民幣一萬一千元。(5)在案之人民幣二千三百元,予以沒收。
判決后,李振有上訴提出,其是從犯,一審判決對其量刑過重。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李振有參與盜竊預謀,積極實施盜竊犯罪及銷贓,并與另三名原審被告人均分了銷贓所得款項,在共同犯罪中,李振有與另三名原審被告人的作用相當,在犯罪過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不能認定李振有為從犯,故該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與已查明的事實不符,不予采納。一審法院根據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李振有、原審被告人董樹平、高紅超、趙艷春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以及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所作的判決,定罪及適用法律正確,量刑及罰金適當,對在案之人民幣處理亦無不當,審判程序合法,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裁定如下:駁回李振有的上訴,維持原判。
審判邏輯
一、爭議焦點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對李振有、董樹平、高紅超、趙艷春的上述行為如何定性,產生了兩種分歧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應該認定為職務侵占罪,另一種意見認為應該認定為盜竊罪。
二、觀點透析
第一種意見認為:董樹平、高紅超、趙艷春是公司聘用的保安員,其崗位職責就是保護公司財產的安全,兩人利用自己擔任保安員的職務便利,在值班期間伙同李振有將公司財產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之規定,構成職務侵占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董樹平、高紅超、趙艷春利用工作上對公司環境熟悉等條件,伙同被告人李振有采用秘密竊取方式,占有公司財物,數額巨大,不屬于利用職務便利,而符合盜竊罪的構成特征。
本判決同采納了上述的第二種意見。主要理由如下:
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規定,職務侵占罪是指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行為,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投;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沒收財產。此處“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主要是指利用自己在職務上所具有的主管或者管理、經手本單位財物的便利條件,如公司的會計或出納利用經手、管理錢財的便利條件,而將公司錢財占為己有的行為。
筆者認為,職務侵占罪與盜竊罪的犯罪客體都是財產所有權,主觀上均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職務侵占罪中的行為人侵占本單位的財物時也會采取竊取的方法,但兩者之間還是有根本的區別:
第一,犯罪的主體不同。盜竊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而職務侵占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是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中具有主管、管理、經手本單位財物職務的非國家工作人員。
第二,犯罪的客體不同。盜竊罪的客體是公私財物所有權;職務侵占罪的客體則僅指行為人本單位的財物所有權。
第三,犯罪的對象不同。職務侵占罪與盜竊罪的犯罪對象都是財物,但職務侵占罪的犯罪對象只能是行為人本單位所有的或占有、管理的他人所有的財物,而盜竊罪的犯罪對象則無此限制。
第四,犯罪的客觀方面不同。職務侵占行為中也有竊取行為,但行為人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施竊取行為的,行為人在以竊取方式侵占本單位財物之前已經合法地持有單位的財物。這與盜竊罪中的竊取行為具有本質的不同。
第五,在犯罪成立上,職務侵占罪和盜竊罪雖然都以數額較大為犯罪構成要件,但在具體數額的認定上,盜竊罪犯罪構成的數額起點要低于職務侵占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盜竊雖未達到數額較大,但多次實施的,依法也構成盜竊罪。
第六,在量刑上,職務侵占罪的法定最高刑為十五年有期徒刑,且只有數額巨大的,才可以并處沒收財產。在盜竊罪的量刑上,只要構成犯罪,都必須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并處罰金或沒收財產。在主刑上,盜竊罪除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的,盜竊珍貴文物,情節嚴重的可以被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外,其他盜竊罪的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
司法實踐中,應注意區分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與利用熟悉工作環境及了解有關信息等方便條件之間的區別。一般說來,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行為人基于其職責而在事實上已經合法地控制了該財物,一旦主觀上產生非法占有目的,其利用這種便利條件即可實現犯罪目的;利用熟悉工作環境,了解有關信息是指行為人僅僅因為工作方便,而較容易接近并非由其持有、保管、使用的本單位財物或了解有關信息,但尚未基于職責而合法地控制該財物,行為人利用這種方便條件并不能直接非法占有財物,只有進一步實施秘密竊取等行為才能實現其非法占有的目的。
本案中董樹平、高紅超、趙艷春對公司汽車的直接占有和掌控,利用的是三人擔任公司保安員的工作便利條件,其占有的行為方式上不符合職務侵占罪的客觀方面構成要件。而盜竊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秘密竊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或多次盜竊公私財物的行為。本案犯罪行為人是在自認為是利用擔任公司保安員的便利條件,將公司汽車偷出后,夜間秘密運出不會被人知曉情況下,占有公司財物。本案中行為人與非法占有的單位財物沒有職責上的權限或直接關聯,僅僅只是利用了工作中易于接觸他人管理、經手中的單位財物、熟悉作案環境的便利條件,則屬于“利用工作條件便利”,并由此實施的秘密竊取公司財產的犯罪,其行為方式符合盜竊罪的客觀方面構成要件。
(蔡寧、程昊)
摘自:賀榮著《侵犯財產罪卷.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典案例分類精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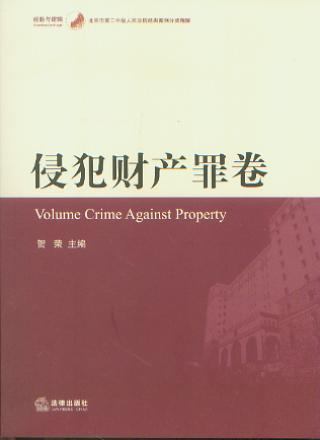 李振有等人盜竊案
李振有等人盜竊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