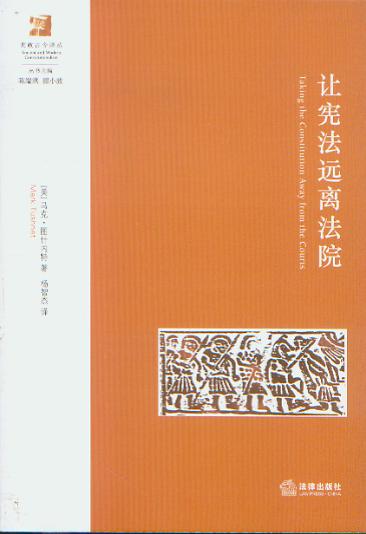
一個沒有違憲審查的世界
一個沒有違憲審查的世界,會是什么樣子?其可能像斯大林主義的蘇俄,或者也可能像沒有成文憲法的英國,或是像有成文憲法但是法院并不執行的荷蘭。我們對沒有違憲審查的世界的想象,會受到自身政治歷史的影響,而我們的政治史中,違憲審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如我所講,最高法院做了之前那樣的聲明,而且我們有好幾年的時間可以調整,那么我們的政治行為,就可能會轉變成我們可以自治的方式。
英國和荷蘭的例子,證明了在不采美國式違憲審查的情況下,也可以發展出有限政府和人權保障的政治系統。部分理由在于,我們可以對政府施加“法律的”限制,而非“憲法的”限制。兩者的差別在于,立法機關可以推翻法律的限制,但不能推翻憲法的限制。
大部分我們所認知的美國憲法,在英國則屬于行政法的內容。英國法院已經發展出一套相當強的“逾越權限”(ultra vires)法,法院對政府官員逾越法律賦予之權限的行為會加以否定。例如,如果一個臥底警察因為某人車燈壞了而逮捕他,則可能會被認為是逾越權限,因為臥底警察并無權逮捕交通違規者。法學教授塞思·克賴曼(Seth Kreimeir)的一項重要研究證實,大部分美國下級聯邦法院所處理的案件,涉及的都是針對低階官僚(包括警察)的案件,而這些案件其實都可以透過英國這種非憲法的理論加以處理。而且成文憲法中的條文可以影響法官解釋法律的方式:當一法律與薄的憲法的沖突越大,法院就會用更多的理由來減少這種沖突。
這些都可以是強而有力的原則。法院可以非常認真,認為除非法律明確授權,否則將認定一行政行為欠缺授權。例如,若只有政策上的授權,則可能無法作為侵入性搜索的正當根據。荷蘭的最高法院就是采取這種方式,認為對在押中的嫌犯偷偷進行錄音,所取得的證據是無效的,因為其屬于必須得到法律明確授權的“激烈措施”。同樣地,法院也可以嚴格解釋授權搜索的法律,認為授權警察對汽車進行搜索,并沒有授權警察搜索扣押中的汽車或者搜索車庫。法院也可以追問立法機關是否對監獄環境有作明確授權,來管理監獄的生活條件。
不過,此時不太可能會發生對逾越授權原則或類似的法律解釋原則的過度濫用。[21]當立法機關介入或者采取法院所希望的規則時,一個無權宣告法律無效的法院什么都不能做:若授權搜索的條文非常明確,那么法官就不能援引逾越授權原則或其他解釋方法來讓其無效。
但是我們必須記住,此時也不太可能會發生對警察行為的憲法限制的過度濫用。美國最高法院允許對扣押車輛進行搜索所根據的判決先例,一般認為是基于一個合理的理由:警察必須有權搜索在高速公路上攔下的汽車;同樣地,對那些不開走車子而可以成功地將犯罪證據隱藏的人,應該也有這樣的權力。可是若用逾越授權的解釋方法,我們就不能說該先例也授權對在押的汽車進行搜索。也就是說,最高法院在主張這項權力時,不會過度濫用。
有時候,判決警察辦案技巧合憲的原因,就是“來自于”違憲審查本身。1996年時,有一個案件是華盛頓特區的便衣毒品警察,將一輛車攔下,說駕駛員沒有專心開車而違反交通規則,最高法院認為這些警察并沒有違憲。事實上,華盛頓的警察規則說,便衣警察不能進行交通違規的逮捕,理由很簡單:如果你是一個在晚上開車的女人,一輛沒有警察標示的車、穿著普通的人想攔下你,請問你會怎么做?
這個案例非常適合援用逾越權限這個想法。但是這么做,會與我們的憲法系統格格不入。批判者會問,一個人是否有憲法權利,怎么會取決于該逮捕或搜索是否有警察規則的授權呢?
法院也有其他理由可能不愿意對警察權力做仔細的憲法限制。美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警察所面對的問題很多。我們曾經放棄了一個全國限速的改革,因為在東北方擁塞的道路上限速55公里或許還算合理,但是在懷俄明州那就很可笑了。同樣地,對華盛頓特區警察權力的合理限制,拿來用到懷俄明州的騎兵上就
不太合理了。法院若援用逾越授權原則,就可以讓懷俄明州的立法機關輕松地對搜索行為進行明白的授權,同時卻不讓市議會這么做。但是,如果對警察的限制已經深深地成為憲法中的一部分,就不太可能采用這種折中方式。
如果法院可以不用援引憲法,他們可能“比較”愿意去規范警察的活動。所以,違憲審查的存在,實際上反而“減少”了我們憲法對政府擴權的限制。[25]
摘自:[美]圖什內特著《讓憲法遠離法院/憲政古今譯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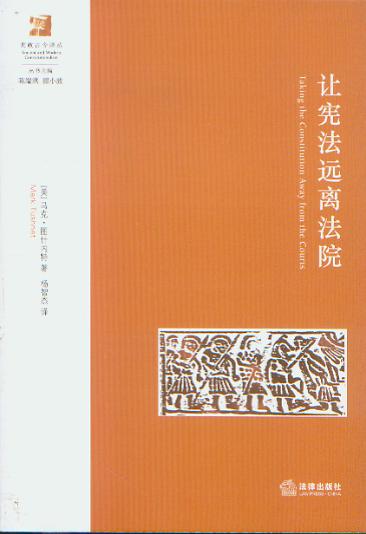 一個沒有違憲審查的世界
一個沒有違憲審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