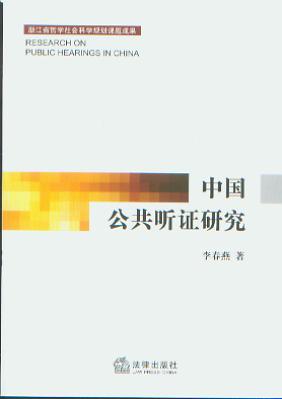
公共聽證對社會公眾的價值
公共聽證對社會公眾的價值可簡單地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公共聽證有利于培養(yǎng)人的主體性意識;二是公共聽證有利于社會公眾獲得“過程利益”;三是公共聽證有利于保障社會公眾的實體權益。
(一)有利于培養(yǎng)社會公眾的主體性意識
人的主體性理論產(chǎn)生于17、18世紀資產(chǎn)階級反對封建專制斗爭中,最初僅涉及倫理學領域,意指某一個體作為一種道德主體所具有的區(qū)別于客體的本質屬性。康德將人的主體性理論由倫理學領域擴展至法律哲學領域,認為一個國家的公民狀態(tài)“先驗地”建立在如下原則之上:(1)社會中的每一個分子,作為人,都是自由的;(2)社會中的每一個分子,作為臣民,同其他任何一個分子,都是平等的;(3)一個普通政體中的每一個分子,作為公民,都是獨立的。德國受康德的人的主體性理論的影響,強調“每一個人都不容許完全被當做工具來對待,而應將其本身當做目標來考量,而他的尊嚴也正好存在于此”,進而在《基本法》中確立了“人性尊嚴不可侵犯”條款。行政參與制度的確立乃至行政程序法的產(chǎn)生,都與人的主體性理論具有密切關聯(lián)。因為,既然是法律關系的主體,就不應聽命于另一方主體的隨意處置,而應被賦予對涉及自己的事務發(fā)表意見的機會。
對于中國來說,“君權神授”、“官貴民賤”、“與世無爭”等傳統(tǒng)政治文化抑制了社會公眾主體意識的形成。①除封建帝王之外,所有的人都依附于另一主體,因此無所謂人的獨立性。解放戰(zhàn)爭時期,雖然有推倒三座大
山、翻身做主人的豪情,但一首到處傳唱的《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揭示了社會公眾對于政府乃至領袖個人的依賴情結。可以說,此時,人的獨立性仍然是有限的,至少沒有——沒有必要有——獨立的判斷能力。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特別是隨著市場經(jīng)濟帶來的私有財產(chǎn)的增多和國家干預的減少,人們逐漸認識到個體的獨立性與主體性。這種覺醒的過程是痛苦的,因為擺脫對另一個主體的依附.,同時也意味著與來自這一主體的某些“庇護”相訣別,并需要身體力行地積極主動地維護自身利益。但無論如何,當市場經(jīng)濟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當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當政府腐敗案在身邊頻頻發(fā)生時,社會公眾認識到“自救”的必要性,認識到通過自身努力改變自身命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此積極地參與公共行政過程。在制度化的參與過程中,如公共聽證,通過與政府辯淪,與專家交流,與普通社會公眾通力合作,社會公眾將逐漸認識到自身的價值,進而產(chǎn)生獨立的主體意識。當主體意識產(chǎn)生以后,“大部分公民寧愿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也不愿別人主宰自己的命運,哪怕別人做的要比自己更好”。②這樣,社會公眾的參與需求將更加強烈。
(二)有利于社會公眾獲得“過程利益”
“過程利益”(pmcess benefits)是邁克爾·D.貝勒斯在論述程序正義的評價標準時提出的一個概念,意指在“負擔/利益決定”程序進行中當事人所獲得的利益。貝勒斯首先論述了對程序的工具主義評價方式,即經(jīng)濟進路和道德進路,但發(fā)現(xiàn)它們都依賴于結果的正確性,這就可能產(chǎn)生如下現(xiàn)象:“如果沒有正確結果或者無法確定何種結果是正確的,那么就應當使用最廉價的程序。”于是,貝勒斯轉而提出“內在過程價值”(:inherentproc3es8 Value)進路,而“內在價值這個概念并不意味著價值是獨立于相關過程的效果或后果的。與道德錯誤成本和經(jīng)濟錯誤成本產(chǎn)生自不正確的決定不同,程序所實現(xiàn)的內在價值是獨立于具體結果的。換言之,從程序到經(jīng)濟及道德錯誤成本的因果鏈需要經(jīng)過具體結果這一環(huán)節(jié),但是從程序到過程價值或利益的因果鏈卻不需要經(jīng)過具體結果這一環(huán)節(jié)。相反,過程的價值是可以建立在這樣或那樣的一個決定已經(jīng)作出這一事實之上的。這種價值是一種源自過程本身的滿足”,①是一種“過程利益”。在若干“過程利益”之中,參與即為其一,即在參與過程中,社會公眾得到心理滿足,進而認可行政行為。之所以提出獨立于實體利益的“過程利益”,是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參與影響的只是未來案件,而獨立于個別案件的正確結果i②簡言之,行政參與(包括公共聽證)與行政行為是否正確沒有必然聯(lián)系,但這并不影響我們積極參與行政程序,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獲得了有利于在實際層面和心理層面解決問題的“過程利益”。這正是法律程序的“過程價值”(13roeess value)所在。
(三)有利于保障社會公眾的實體權益
“在國家機關作出各項實體決定時,公民只有被尊重為法律程序的主體,享有充分地陳述意見、辯論等參與機會,才能真正捍衛(wèi)其基本人權。”④對于這一點,學術界和實務界已基本達成共識。因為在行政程序中,社會公眾通過向行政機關陳述有關事實,陳述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有利于行政機關掌握事實真相,進而作出正確的行政行為,維護社會公眾的實體權益。或者說,“如果受行政行為潛在影響的各關系人,被允許以有意義的方式參與行政機關的決策過程,那么行政機關就比較無機會根據(jù)不正確的事實作判斷,或以不完整的分析采取行動”。①需要注意的是,通過行政參與程序保障社會公眾的實體權利,并不意味著社會公眾的所有要求都能夠得到滿足,因為作為行政機關來說,必須在實現(xiàn)社會公平的前提下,綜合考慮公共利益與個人之間、公共利益之間以及個人利益之間的取舍,而非以維護某個或某些社會公眾的利益為己任。
摘自:李春燕著《中國公共聽政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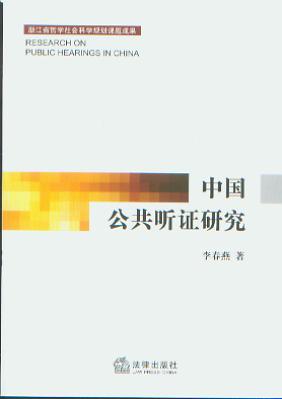 公共聽證對社會公眾的價值
公共聽證對社會公眾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