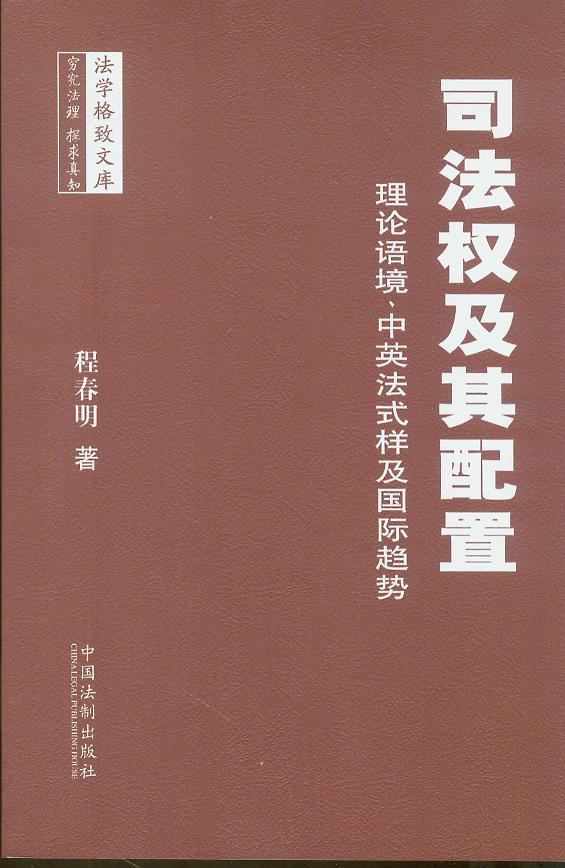
市場自由主義邏輯下的司法權
因此,如果我們用三權分立制度的框架來研究和解釋中國司法制度的歷史和現實,似乎缺乏解釋力。取代三權分立這一理論范式,試圖重新理解和解釋司法制度對近現代中國社會意義的,在我們看來,是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范式。這種理論范式繼承了三權分立理論引進者們所具有的民族主義的內涵,但是用經濟系統取代了三權分立制度所代表的政治系統。對他們而言,這種取代是正常的,并且是名正言順的。
最全面、系統論證這種經濟自由主義范式及其和中國相關性的是華人學者黃仁宇先生。黃仁宇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中詳細探討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方興起和發展的整個過程,也詳細分析了西方學者所作的關于資本主義的種種學說。黃仁宇認為現代資本最早起源于威尼斯,中經荷蘭,而最后在英國成熟。而從資本主義的最后成型階段的英國來考察,則可以發現要從前資本主義的農業體制轉化到資本主義體制,必須“一方面必須將其上層結構改組,以便迎合新法制,通常也要翻轉其底層結構,以便產生能夠互相交換的局面,更要經過一段司法與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間關系密切聯系,也才能使以上三個原則順利發展,通過財政稅收幣制諸種政策,使公私互為一體。”①至此時,“整個國家方能夠用數目化管理”。②因此,黃仁宇也概括出了資本主義必然具備一種技術性格,這種技術性格又具體表現為三個特征:(1)資金廣泛的流通,剩余之資本透過私人貸款的方式,彼此往來。(2)經理人才不顧人身關系的雇傭,因而企業擴大超過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監視之程度。(3)技術上支持因素通盤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師事務及保險業務等,因此各企業活動范圍又超過本身之能及。①以上三個條件,又全靠信用,而信用必須依賴法治維持。②黃仁宇關于資本主義的思考,首先得益于他對明朝稅收制度的研究和思考,之后,并受到了李約翰博士的啟發。③
用這種分析框架,黃仁宇在系統研究了中國歷史之后用一種散文的筆調系統反思了中國從商周一直到近代國共兩黨的合作和抗爭。對黃仁宇來說,由于特殊的15英寸等雨線的存在,使得農耕的中原地區和周邊游牧民族生活的草原地區區分開來,因此使得世界上最長的國防線的存在成為必要,也因此催化出一個統一的集權的中央政府。由于黃河以及黃土高原的存在,使得黃河水災的泛濫成為整個中原地區必須共同面對的大事,也使得統一的中央集權的中央政府,對務農的中原地區來說顯得必要。正是由于這兩個內外原因,使得中國早在秦朝的時候,就建立了現代意義的集權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④但是這種政治上的早熟,從長遠的眼光來講,給中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因為這種中央集權的政府,表面上看起來相當強大,其實力卻以對大批小自耕農征稅和抽調人力為準。基于這個原因,如何保證強大的國家權力能夠直接面對原子化的小自耕農,便是漢代之后中央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之后政府打擊和限制地方上的鄉紳勢力,以及重農抑商,都可以從中得到解釋。⑤另外,由于當時科學技術以及交通等等的諸多限制,也使得中央政府日常管理國家能力相當有限,不得不在技術之外,依靠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方式來統治。這種統治特征和性格,也影響到了法律和司法在中國的命運。因為對傳統中國來說,小農固然請不起律師,官僚組織也無力創制復雜的治理理論。因此中國的政府,往往以道德代替法律,更以息爭的名義,責成里長甲長鄉紳將大事化了,小事化無。一方面將衙門的工作分量減輕,一方面則阻塞底層社會里各種經濟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只因為最原始型的交換才能被眾目公認,稍帶現代型的分工合作,及于較繁復的契約關系,即無社會之保證。)①因此,對于傳統的中國來說,獨立的并且有國家強制力在背后作保障的司法制度,始終不可能形成。而這樣一個司法制度,對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來說,則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
也是憑借這個分析框架,使得黃仁宇為中國百年來的憲政實踐的失敗找到了一個理由,那就是雖然整個國家的上層制度已經得到了改進,但是因為整個國家的下層,始終沒有得到變換,所以上層的改革始終缺乏下層改革的支持,使得中國的憲政改革始終停留在名存實亡的尷尬境地。盡管如此,黃仁宇還是認為,國民黨領導的民國政府,已經對中國的上層政治結構,進行了相當徹底的改革,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則相當徹底地改革了中國的下層社會。今后中國改革的方向,是如何將兩個各自做了徹底改革的上層和下層進行改組,徹底改變黃仁宇所說的“潛水艇夾肉面包”的狀況。②而所謂的中層機構,不外乎就是各種交通設施、銀行、以及司法制度等各種服務于經濟系統的技術支持。
黃仁宇沒有詳細說明他所說的法律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具體含義。不過從黃論述的字里行間,或許我們能夠預見,他所說的法律,首先是要保障私人的財產權益,其中所言的法律上的公平,則被限定在經濟交往的公平之中。其次,必須具備一定的形式特征,具有穩定性和可預見性。我們或許可以將這種法律概括為“自由主義+形式主義”。如此,司法制度在黃仁宇的法律觀念之中,或許比立法制度具備更加實質性的意義。立法制度或許可以在革命之中顯示出力量,但是在常規的市場經濟中,以法律職業共同體為支撐的司法制度或許更能夠體現法律的這種技術特征和信用特征。甚至法律最后就是一種確定的知識體系,可以恒久不變,也不受變化無端的民主制度的干擾。①而法律制定的過程,法律專家所起到的作用,更要強于議會制度中的人民代表。在這種經濟法律觀中,民主制度實際上已經被架空,而法治精神也脫離了和民主精神的內在聯系。如此,中國即使沒有成熟的民主制度,也可以有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司法制度存在。黃仁宇雖然沒有明說這層含義,不過也離此不遠了。
往后中國發展的經驗,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驗證了這種推論,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之中國。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思路確立之后,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正在逐漸加強。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各種法律制度,尤其是和經濟改革相關的經濟法律制度逐漸完善,甚至包括像破產法和金融法這種相當前沿的制度也正在逐漸發展和完善。之后“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的提法逐漸正式化和官方化,在1997年,中央政府提出“依法治國”、“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并且提出將法治作為中國的基本治國方略。因此,就司法制度來說,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司法改革,首先是和經濟活動關系密切的訴訟制度的改革拉動起來的,而所謂的司法公正,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內容,也是經濟活動中的司法公正。②在刑事審判中的公正問題,盡管一直有相當多的學者關注和努力,但是總是不如民事制度的改革來得快,來得及時。之后,中國的經濟隨著市場化的深入一路迅猛發展,各種立法也逐漸完備,司法制度尤其是民事司法制度的逐漸發展,則確實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③而改革開放之后,經濟自由主義思潮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生存并形成一定的影響,與其和市場經濟邏輯上的某種契合不無關系。
摘自:程春明著《司法權及其配置;理論語境、中英法式樣及國際趨勢/法學格致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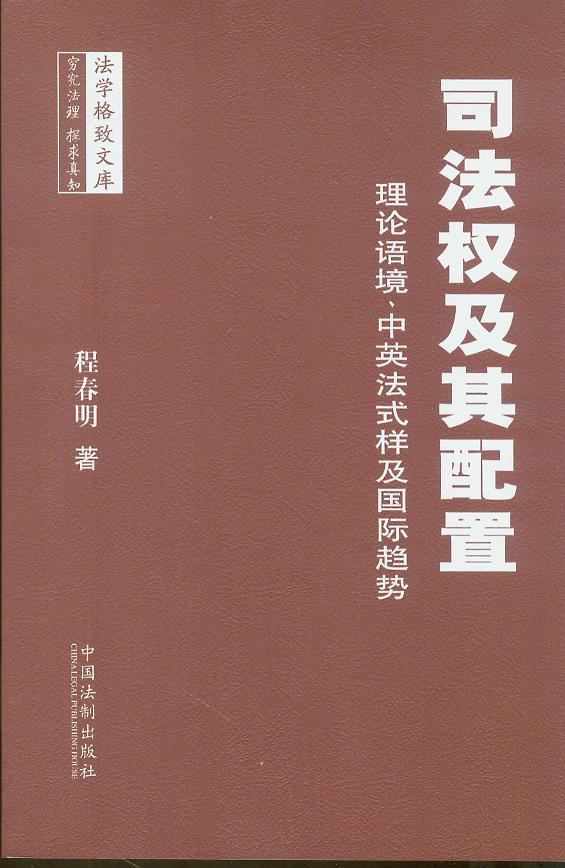 市場自由主義邏輯下的司法權
市場自由主義邏輯下的司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