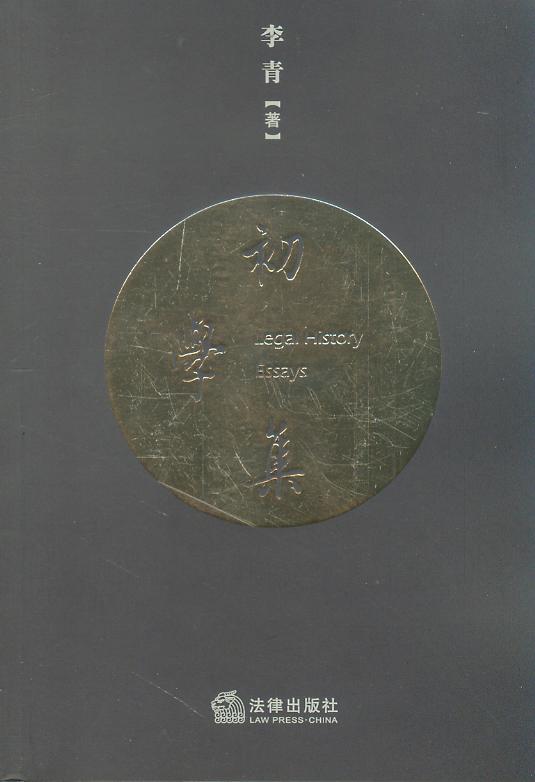
沈家本與比較法學
2004年是沈家本逝世90周年。為了紀念這位法學大師,撰寫此文。
沈家本通曉中國傳統法律,是“以律鳴于時”的著名法學家,不僅是對中國傳統法制進行批判總結的第一人,還是“會通中西”修訂法律的主要負責人,中國法律通過他與西方法律接軌,因此,中國法制的近代化有他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本文僅就他對近代比較法學的研究開拓談談意見。
中國古代法是在縱向比較中發展的,無論是漢承秦制,還是清襲明制,甚至是唐宋法制都是如此,但是缺乏橫向的比較,即使是在沈家本之前薛允升的《唐明律合編》,也使用的是縱向比較的方法。在橫向比較上,沈家本是開拓者之一,他通過中西法律的橫向比較,把修律心得貫穿在仿效西方法律上。
沈家本(1840~1913年),曾任刑部左侍郎、大理寺正卿、刑部右侍郎、修訂法律大臣等職,他生活的年代正處在中國社會由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激烈動蕩時期,西方的先進法律、法學的輸入,使中國傳統法律面臨尖銳的挑戰,沈家本針對當時墨守成規、固守中法、詆毀西法的守舊勢力,認真考察了中國傳統法律的沿革得失,通過與西方法律的比較,客觀地指出:“方今世之崇尚西法者,未必皆能深明其法之本原,不過借以為炫世之具,幾欲步亦步,趨亦趨。”批評清朝內部的那些拘泥舊法,鄙薄西方的守舊者“以為事事不足取”,“抑知西法之中,固有與古法相同者乎?”[1]他以務實的態度,闡述了會通中西法律的重要性。他說:“當此法治時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討中法,則法學不全,又安能會而通之以推行于世?”[2)“余奉命修律,采用西法互證參稽,同異相半。然不深究夫中律之本原,而考其得失,而遽以西法雜糅之,正如枘鑿之不相入,安望其會通哉?是中律講讀之功,仍不可廢也。”[3]
1.比較法學的提出與晚清的同文館教育分不開
同治元年八月(1862年),清政府為了培養洋務人才,開設了同文館。同文館正式開館時,就被作為總理衙門的附設機構,因此,在同文館內設有英文館、德文館、俄羅斯文館、東方文館,以及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班,后又增設天文算學館、醫學館、化學館。同文館的教師多為外國人,由總稅務司英人赫德推薦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總管教務近三十年。同文館教授外國語言,打開了中國學習西方的語言通路,同時,同文館還引進西方的法學教育,為了培養熟悉中外法律、具備近代國際法知識的洋務人才,同文館把國際法作為一門重要課程,所使用的教科書,就是《萬國公法》。當《萬國公法》譯出后,呈送給恭親王時,恭親王大悅,稱道:“此乃吾所急需也。”“雖然此書所記之外國律例,與中國體制大不相同,仍不乏有用之處。”[0]隨即下令刊印三百冊,分發各省官員。《萬國公法》的問世,標志著近代西方國際法著作第一次被完整地介紹到中國,因而在中國法律近代化的進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時也使中國學生在學習外國語言的同時,了解和掌握了當時歐美最新的國際法專業知識,傳播了西方的法文化。
同文館以翻譯西方法學著作作為了解西方國家情況和輸入西學的重要途徑,1880年同文館教習法國人畢利干翻譯了第一部西方法律《法國律例》,內容包括刑律、刑名定范、貿易定律、園林則律、民律、民律指掌。這一時期譯介的西方法學書籍還有:《公法便覽》、《公法千章》、《星軺指掌》、《中國古世公法》、《陸地戰例新選》、《公法總論》、《各國交涉公法》、《各國交涉便法》、《比國考察犯罪記略》、《西法洗冤錄》、《法使指南》、《歐洲東方交涉記》、《中西文化略論》、《英俄印度交涉書》、《佐治芻言》、《國政貿易相關書》《美國憲法纂釋》、《各國交涉公法論》、《東方交涉記》等,[1]并出版了《西政叢書》、《質學叢書》、《西學富強叢書》等專論法政或法律的西學叢書。此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當時譯為《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當時譯為《萬法精神》)、斯賓塞的《代議政體》(當時譯為《原政》)、《美國獨立宣言》(當時譯為《美國獨立檄文》)等也在這一時期被相繼介紹到中國。
同文館教育,用最簡潔的方式,開辟了中國認知西方法文化的最直接的渠道,法學著作的翻譯,對近代比較法學有直接的促進作用,給比較法學的開展,提供了一個可能環境。
2.翻譯西方法學書籍和考察外國司法制度,為比較法學研究創造條件
沈家本把改變清朝每況日下的希望寄托在修律上,并視學習西方法律為匡時之任,確立了“參酌各國法律,首重翻譯”的指導思想,組織成立了編譯所,大量翻譯西方法學書籍,在沈家本主持修律期間,共翻譯了幾百種(部)外國的法律法規和法學著作,據沈家本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刪除律例內重法折》記載,修訂法律館“自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一日開館以來,各國法律之譯成者,德意志日刑法,日裁判法,俄羅斯日刑法,日本日現行刑法,日改正刑法,日陸軍刑法,日海軍刑法,日刑事訴訟法,曰裁判法,日裁判所構成法,日刑法義解,校正者法蘭西刑法。至英、美各國刑法……該二國雖無專書,然散見他籍者不少,飭員依類輯譯,不日亦可告成”。至光緒三十一年五月,修訂法律館開館二年零一個月時,沈家本在《修訂法律館情形并請歸并法部大理院會同辦理折》中又對其翻譯成果作了介紹,這時已譯完成和未譯完成的法律又有四十多種。光緒三十三年至宣統元年,翻譯成果更加卓著,涉及的法學領域也更加廣泛,有刑法、民法、商法、海商法、國際私法、行政法、歸化法、票據法、公司法、破產法、國籍法、監獄法、刑事訴訟法等實體法和程序法。譬如《德意志刑法》、《德意志裁判法》、《日本現行刑法》、《日本改正刑法》、《日本商法》、《德國海商法》、《英國公司法論》、《美國公司法論》、《普魯士司法制度》、《日本監獄法》、《奧國國籍法》、《美國破產法》、《日本票據法》、《日本現行刑事訴訟法》、《日本現行民事訴訟法》、《德國強制執行及強制競拍法》、《法國民法總則條文》、《法國民法身份證條文》、《法國民法失蹤條文》、《法國民法親屬條文》、《奧國法院編制法》、《美國刑法》、《比利時刑法》、《芬蘭刑法》等,其中《比較歸化法》和《各國人籍法異同考》就是兩部西方的比較法學專著。
沈家本認為:“方今中國,屢經變故,百事艱難。有志之士,當討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國制度,觀其會通,庶幾采擷精華,稍有補于當世。”[1]這些部門法的引進,為打破中國傳統的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法典體例,建立中國近代法律體系,提供了重要依據。
除了大量翻譯外國法律外,沈家本還積極派人出國考察外國的司法制度。中國自洋務運動時起,首開向海外派遣留學生的先河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了解和學習西方的途徑更加直接和通暢。由于沈家本認為“日本舊時制度,唐法為多,明治以來,采用西法,不數十年遂為強國,是豈徒慕歐法之形式而能若是哉”。且“日本立國之基,實遵守夫中國先圣之道”,“其立憲政體,雖取于英德等國,然于中國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墜。是以國本不搖,有利無弊,蓋日本所變者治法,而非常經,于圣訓正相符合。是中國輿論亦以日本之變法參琢得宜,最可仿效”0[1]因此,輸送了大批法科留學生赴日本、美國、英國等國學習,回國后委以重任。1906年以修定法律館的名義,派董康等人東渡日本,遍訪日本著名的法學家松岡正義、青浦子爵、小河滋次郎、齋藤十一郎等,專門考察了日本的訴訟制度和監獄制度。董康等人回國后,根據考察結果,撰寫了重要的法學著作《監獄訪問錄》、《裁判所訪問錄》、《日本裁判沿革大要》、《日本裁判所構成法》、《獄事譚》等。沈家本在為其作序的序文中,比較了中日兩國訴訟和監獄制度的異同,肯定了通過科學考察,引進外國法制的做法是借以取彼法之善,彌補我法之不善。經過實地考察,推動了清末監獄制度的改良,對清末審理刑事案件的司法實踐,產生了巨大影響,從而掀起了引進和翻譯日本法學著作的熱潮。
3.提出開展比較法學的原則
在對中西法律綜合比較的基礎上,沈家本經過不斷的探索和思考,得出了中西法律可以互補的真知灼見,提出開展比較法學的原則。即:“我法之不善者當去之,當去而不去是之為悖。彼法之善者當取之,當取而不取是之為愚。”沈家本通過比較研究,認為西方法律是西方之所以強盛的重要原因,他贊賞日本“明治以后,采用歐法”,“君臣上下,同心同德,發憤為雄,不惜財力,以編譯西人之收,以研究西人之學,棄其糟粕,而擷其精華,舉全國之精神,胥貫注于法律之內。故國勢日張,非偶然也”0[0]因此中國法律必須“幡然變計”。例如,沈家本從中西法律的對比中發現“方今環球各國刑法,日趨于輕”,而“中重西輕者為多”,他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較之中國的封建舊律文明和進步,應該“取人之長以補吾之短”,沈家本在中國歷史上輕刑思想的基礎上,吸收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古典刑法學派進步的輕刑思想,將舊律中的笞、杖、徒、流、死五刑,改為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面對“歐美刑法,備極簡單”,而舊律死罪條目繁多的差距,在新刑律中酌減死罪條目,執行死刑唯一。沈家本希望中國效法謠方的法治,以輕刑治國,他說:“刑法乃國家懲戒之具,非私人報復之端。若欲就犯罪的手段以分刑法之輕重,是不過私人報復之心,而絕非國家懲戒之意。”(1]從主觀上否定了“以刑為泄憤之方”的封建刑法的報復性和隨意性。沈家本還以西方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原則,廢除了舊律中援引比附的制度,提倡實行懲治教育。
沈家本的修律活動,較充分地貫徹了“參考古今,博稽中外”,融會中西的修律宗旨,他說“當此法治時代,若但證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討中法,則法學不全,又安能會而通之,以推行于世”o[2]他認為,學習和借鑒西方法律,并不是意味著拋棄中國的法律傳統,“西法之中,固有與古法相同者”,[3]他指出:“吾國舊學,自成法系,精微之處,仁至義盡,新學要旨已在包含之內……新學往往從舊學推演而出,事變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總不外情理二字。無論舊學、新學,不能舍情理而別為法也,所貴融會而貫通之。”[4]他強調:“中學多出于經驗,西學多出于學理”,“不明學理則經驗者無以會其通,不習經驗則學理亦無從證其是。經驗與學理正兩相需也”o
4.突出比較法學的社會功效
比較法學源于西方國家,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但自古希臘比較法學興起至19世紀這段時期,比較法還未形成一門學科,比較法學偏重于對法理的考究。19世紀中葉,歐洲大陸國家適應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為了開展廣泛的法典編纂活動,對不同國家的法律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比較研究,資本輸出、殖民地擴張和國際貿易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比較民法、比較商法等比較法學的興盛。
鴉片戰爭以后,以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的先進的中國人,開眼看世界,為了讓中國人了解大洋彼岸的世界,在其所編著的《四洲志》、《海國圖志》、《滑達爾各國律例》、《華事夷言》等著作中介紹了有關西方的信息,這是中西比較的最初萌芽。梁啟超、嚴復等維新派代表人物則更多地關注于西方的政治制度,為變法維新提供可資借鑒的模式。只有沈家本站在中西法律文化沖突融合的潮頭,高屋建瓴,把中國的法律問題放在世界范圍內進行考察。
對法律進行比較研究,不能脫離歷史發展的背景即法律所依賴的社會基礎和法律發展的階段性,正如法國比較法學家羅迪埃爾指出的那樣:“人們不應該比較外國法律中脫離歷史和文化背景的孤立的規則。必須從這些規則所屬的法律整體中去比較它們,并且根據它們所依賴的歷史發展去比較。”[1]沈家本對于西方權力分治的闡述,其用
意不僅在于改革晚清的司法,也是向晚清的預備立憲進言。他說:“近今泰西政事,純以法治,三權分立,互相維持。其學說之嬗衍,推明法理,專而能精,流風余韻,東漸三島,何其盛也。”[2]他認為:“東西各國憲政之萌芽,俱本于司法之獨立”,“司法獨立,為異日憲政之始基”,[3]l‘西國司法獨立,無論何人皆不能干涉裁判之事,雖以君主之命,總統之權,但有赦免,而無改正”o[0]他認為,清朝的官制“以行政而兼司法”,不符合清末立憲的要求,他根據司法獨立的原則,積極營建審判獨立的司法制度,在其主持制定的《法院編制法》中,明確規定各審判衙門“獨立執行”司法權,行政主官及檢察官“不得干涉推事之審判”。
必須指出,沈家本對“西法”的理解還是膚淺和不全面的。他在《法學名著序》中,概括地表述了對于中西法律的基本認識。他說“抑知申韓之學,以刻劾為宗旨,恃威相劫,實專制之尤。泰西之學,以保護治安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乃人人不得稍越法律之范圍。二者相衡,判然個別”。這里沈家本看到了中國的封建專制法律與西方的資本主義的法律的不同,但是由于缺乏對西方近代法制的本質、社會基礎及其文化的了解,沈家本不能也不可能對西方的法制或法學作出系統的論述,不僅如此,他還往往以西法比附中法而顯得牽強,如他說“舉泰西之制,而證之于古”,[1]‘‘古法之中,固有與古法相同者”。[2]他曾以《周禮》中的“三刺之法”,比附西方的陪審制;以漢之讀鞫乃論,唐之宣告犯狀比附西法的刑之宣告;以唐宋時期刑部及大理寺的分工,比附西方行政與司法的權限相分。沈家本甚至將把“日本全國新制,萃于《法規大全》一書”,視為是集《周官》、《通典》、《會典》諸書之流亞也0[0]沈家本的上述觀點雖有不成熟乃至錯誤之處,但同時也反映出他借古喻今,以期減少修律阻力的良苦用心。譬如,就刑罰而言,沈家本指出古代圣賢之君及有道之君皆用刑輕,而昏暴之君用刑重,橫向比較“中重而西輕”,因此,在他的主持下,“改重為輕”,刪除了中國歷史上行之已久的凌遲、梟首、族誅、緣坐、刺字等酷刑,使中國的法制文明向前邁了一大步。沈家本在《重刻明律序》中清晰地表達了這種意向:“方今環球各國,刑法日趨于輕,廢除死刑者已若干國,其死刑未除之國,科目亦無多。此其故,出于講學家之論說者
半,出于刑官之經驗者半,亦時為之也。今刑之重者,獨中國耳。以一中國而與環球之國抗,其優絀之數,不待智者而知之矣。”
在中國近代史上,林則徐是首倡“睜眼看世界”的思想家,沈家本則是睜眼看世界法律的思想家,他從中西法律的比較中,提倡擇善而從,他不僅是采用中西法制比較研究方法的第一人,也是“會通中西”,仿西法主持修律的改革家、實踐家,沈家本對中西法律的比較的有益探索,又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啟示。他的歷史地位,正如楊鴻烈先生評價的那樣:“沈氏是深了解中國法系,且明白歐美日本法律的一個近代大法家,中國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啟后,并且又是媒介東西方幾大法系成為眷屬的一個冰人。”
沈家本在修律中,不僅會通中西,使中國法制走向近代化的開端,而且他還主張以舊律學為根底,學習西方法學,力爭在法理學上有所突破,所以,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沈家本都不愧為中國近代比較法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
摘自:李青著《初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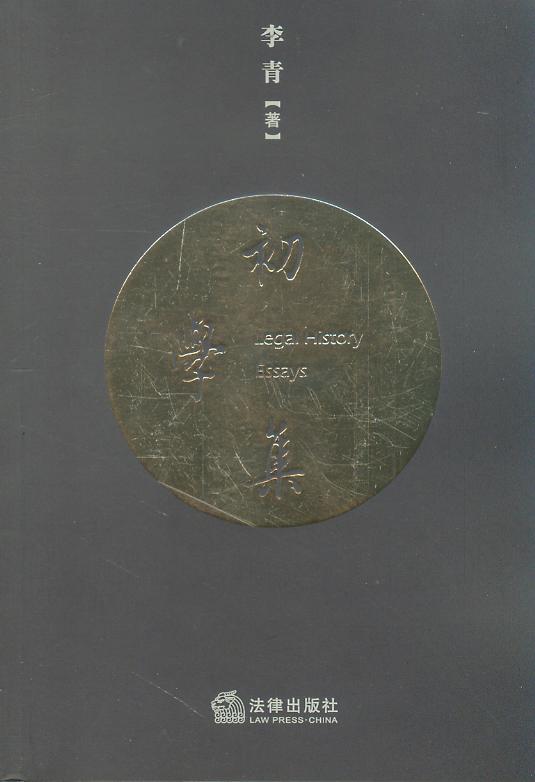 沈家本與比較法學
沈家本與比較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