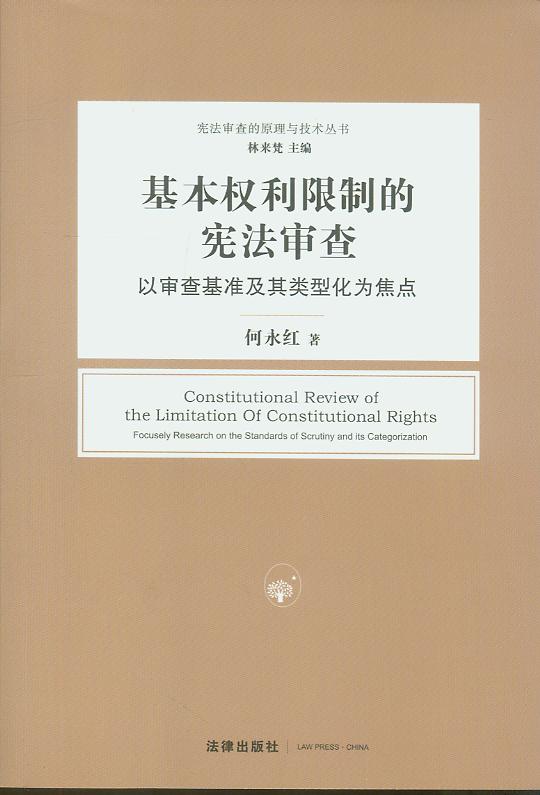
圍繞規范證立價值:各種事實因素的關系脈絡
眾所周知,德國深受歐陸傳統法教義學理論思維的影響。從本書述及的眾多憲法判例中我們亦不難發現,聯邦憲法法院總是以基本法規范或憲法規范理論為切人點,進入案件的事實因素分析,同時,這種分析也始終圍繞所涉規范性命題,借助于事實因素的橋梁,最終將基本權利價值從規范上的應然狀態演繹推導出實際案件中的類型化控制基準。因研究能力有限,本書在此僅以“事實因素”為關注焦點,試圖通過對前述憲法判例和學說細致梳理,發現其中隱藏的類型化方法。
概略觀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憲法判決中曾以如下因素來界定審查基準的強度:@“所涉及事務領域的特性”、“作成充分判斷的可能性”、“相關法益的重要性”@以及為許多學者支持的“基本權利的干預程度”。當然還有部分學者主張基本權利的“單一面向/多元面向”或是“主觀法面向/客觀法面向”之區分來界定審查強度。@乍看之下,這些界定審查基準的因素零亂無序,難分主次。其實,如吾人所知,德國大多數的憲法判例都是以基本權利的憲法價值原則或是基本法規定的實體法規范理論作為推論基礎,同時雄居主流地位的學說(實體法觀點學派)對其也是大力給予支持的。前文通過“相關法益的重要性”來界定審查基準正是這種規范性理論之體現,其實質乃是以實體法所確立的價值秩序為一般性判斷基準,實現憲法保障人權的基本使命。因為“相關法益的重要性”之因素直接與憲法規范理論相連,所以我們就自然可將之與其他事實性因素區別開來,同時,應將之視為一種根本性或一般性判斷基準,使其統領或引導其他事實性因素作為次級基準的判斷方向。
那么,由權力分立原理所派生出來的、受到學說較大的支持同時也為憲法法院的判決所接受的功能法理論是否能和實體法規范理論并立成為根本性或者說一般性判斷準則呢?筆者對此持否定看法。因為功能法理論所涉及的主要是權力分工不同所產生的特殊決策結構下,法院因對政治性問題或政策性問題不便介入而采取的判斷回避態度或日司法消極立場,所以其并非作為獨立之因素決定基本權利限制的審查強度,它運行的邏輯仍然是以實體法規范理論為基礎。也即當具有“充分判斷之可能性”的情況下,就照實體法規范理論的一般性判斷基準決定審查強度;若情況相反,則因避免作出自己的憲法判斷而使實體法確立的一般性基準無適用余地。故從根本上說,功能法理論是依附于實體法理論,是特定領域實體法理論的消極實現形式。
至于“所涉及事務領域的特性”問題,其實,它是兼具實體法與功能法特征的事實因素。例如,經濟規制較精神自由適用更寬的審查基準,是因為經濟規制具有較強的政策性,法院不宜代行判斷;同時也是由于精神自由具有比經濟自由更高的價值重要性。再如,政治統治的事務,特別是國防與外交領域,適用寬松的審查基準,亦是由政治部門需要對變動不居的政治局勢作機動反應而法院無“充分判斷之可能性”使然。這些領域的審查基準決定的實質因素均能上溯到實體法或功能法結構上,因此,該項因素可以化解為上述兩個因素而無獨立存在之必要。
“基本權利的干預程度”是對基本權利的類型化審查進行精確評價之實質性因素,它甚至可以說是對基本權利的審查強度起決定性作用的評價因素,因為它契合了憲法對人權保護的規范理念。聯邦憲法法院對“干預程度”的細致衡量準則有:“干預措施所造成的損害程度”、“干預時間的長短久暫”以及“所干預的是‘既得的權利狀態’還是‘可能狀態”’等。但這些精細化準則最終均凝聚成一項抽象性評價準則,即“干預措施觸及到的是所涉基本權利的保護領域之‘核心’還是‘外圍’部分”。@
順著憲法規范保護人權理念的整體脈絡而下,我們可以看到,以基本權規范(理論)為依據,構建的一般性之類型化審查基準,其主脈延展之下,是具體案型中“基本權利的干預程度”的細膩化衡量準則,這些準則最后匯集成基本權領域的核心理論,使基本權利限制的一般性之類型化審查基準再次衍生出更為細膩、客觀和精確的類型化基準。當然,除此之外的其他因素,我們絲毫不能否定,也不可忽視其在決定審查強度的參考作用,只不過它們終究只是上述主脈下衍生出的支脈或是上述因素的一個演變形態而已。
有必要強調的是,如上所梳理出的類型化方法推演的模式只是一種簡單化了的形態,現實中不可能具有如此規整的、有如數學公式般的精確基準。吾人所期望的,是通過將基本權利限制的審查基準之精細類型化,使判斷盡量趨于客觀性、合理性而減少恣意性。
摘自:何永紅著《基本權利限制的憲法審查:以審查基準及其類型化為焦點/憲法審查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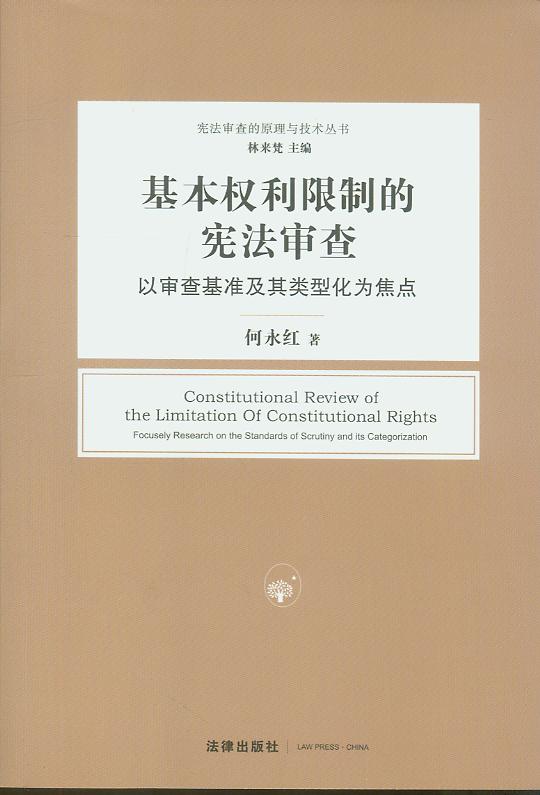 圍繞規范證立價值:各種事實因素的關系脈絡
圍繞規范證立價值:各種事實因素的關系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