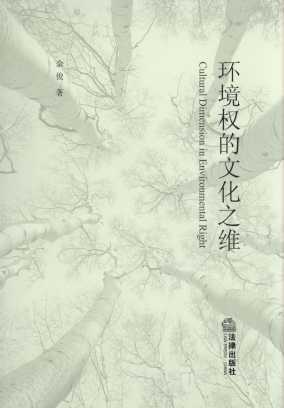
求同存異的法移植
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受到西方發達國家法律文化的沖擊,因此其命運多舛,幾乎為西方強勢法律文化吞并。西方法律文化對中國的沖擊形成了三個前后相繼、互為聯系的沖擊波,第一個沖擊波從鴉片戰爭始到戊戌變法。第二次沖擊維新運動失敗后到辛亥革命。第三個沖擊波以1915年新文化遠動為起點,把宣傳西方民主法治文化精神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猛烈批評結合起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西方法律文化沖突、融合、揚棄、創造的過程,將中國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是中華法系現代化的主要參照體系,環境權觀念和制度的建立就分別吸收了這兩大法系的先進成果。近代中國所繼受的西方法律文化,對于西方來說體現了人類性與民族性、世界性與本土性在一定程度上的統一。移植到中國來,其人類性、世界性的一面應弘揚,其民族性、本土化的一面會改變,其間有著無法回避的矛盾。因此,法律移植是一個“求同存異”的過程。
清末改制、民國六法全書的制定,將中華法系納入大陸法系文化圈內。大陸法系,又稱民法法系,其主要特色是有一部系統的民法典。中國自清末到民國,先后編纂了《大清民律草案》、民國《民律草案》和1929—1931年的《中華民國民法》,法律體系從一開始便受到了大陸法系的影響。中國選擇大陸法系的法律模式,是與中國悠久的法典編纂文化傳統相吻合的。與法的其他形式相比,法典是中國法律文化中最大的本土資源。戰國時期中國就有了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經》,秦律、漢律都是在《法經》的基礎上擴展。以《唐律疏議》為核心的唐朝法律更是成文法典的完美之作,其影響遠播到東南亞地區。法典在中國法律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法典文化在中國歷史上綿延不絕,成為中華法系文化的瑰寶。在中華法系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中國之所以選擇大陸法系的法典化立法模式,固然有政治、經濟和人為等因素,中華法系與大陸法系在法典文化方面的相似也是重要原因。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當時的歷史背景等多種原因,廢除了民國時期的“六法全書”,但大陸法系的思維模式影響仍在。改革開放后,1986年全國人大就制定了《民法通則》,從法律形式上回歸到大陸法系。
不過,中國法典文化的傳統是對刑法文化而言的,中國封建法典是“以刑為主”、“重刑輕民”,法律是用來“定分止爭”而不是維護“權利”。權利是人欲的體現,它不一定合“天理”。在大陸法系國家,民法是私法,是自然權利的體現,法律是用來限制“權力”和確認“權利”。“民法是整個法制的基礎,法的其他部門只是從民法的原則出發并較不完備地發展起來地,民法曾長期是法學的主要基礎。”【1]勒內·達維德將民法比作“法律的真正心臟”。[2]西方從古到今一以貫之的精神內核,這就是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自由首先是個體的自由,它在于自由意志。自由不僅具有消極的意義(自在,擺脫他物的束縛),更具有積極的意義(自為,通過活動實現自己的目標)。不過如果我們的活動缺乏了理性,將會淪為任意妄為。理性的本質是對“一”(統一性)的追求,最關鍵的是,它一定要通過語言和邏輯去追求。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相伴相隨,從根本上規定了西方人。中國傳統文化追求的所謂自由,由于缺乏自由意志(道禪是“無意志的自由”,儒家是“無自由的意志”),只是一種虛幻的自由感。傳統文化也缺乏理性精神。[3]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法律移植原則基本上是“求同存異”,一方面“注重世界最普遍之法則”和“原本后出最精確之法理”,另一方面“求最適于中國民情之法則”。所謂的“普遍之法則”和“后出之法理”實際就是大陸法系的原則和法理,“中國民情之法則”就是宗族主義,在中華法系的近代化過程中,始終貫穿著宗族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矛盾與協調。
大陸法系國家民法中私權神圣的觀念和制度促進了中國權利意識覺醒,打破了“重刑輕民”封建法律文化對人性的桎梏,這應該說是中國移植大陸法系國家法律制度的主要成果。可不知為何,法律移植變得更重視形式,形成了這樣一種錯誤邏輯:由于大陸法系有民法典,所以中國也應該有民法典;大陸法系有了環境法典,中國也就應該有。例如,法國1976年將源于民法的關于農業、森林、礦業等自然資源法規整合為《自然保育法》,1998年又制定《法國環境法典》,將單行公害防治法規與自然保育法一起匯編。于是,我國許多學者便呼吁在中國也制定一部環境基本法典。這些學者認為:隨著環境問題的加劇,我國相繼出臺了《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和《環境影響評價法》等專門性的環境法律法規,大量單項立法需要綜合性立法來統領。而我國現行的1989年《環境保護法》只是法律,不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且調整內容主要是污染防治,不能涵蓋資源、能源的節約利用與保護。在自然資源立法方面,我國目前也沒有統一的《自然資源保護法》,只有一些分散的資源保護法律,如水法、森林法、自然保護區條例,等等。而自然界是一個整體生態系統,對生態資源要素的片面保護是不夠的。以水資源的保護為例,水法不能僅僅規定水資源的節約利用,還要保護好水流域發源地的森林和水流域周邊的濕地。缺水和洪澇威脅等水危機的發生,與生態環境的破壞有很大的關系。借鑒法國這一大陸法系國家的經驗,我們應該制定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法典》,保證環境各單行法之間的協調和統一。
筆者并不反對這些學者的觀點,只是想強調一下在重視形式的時候別忘記了內容。法律形式不同,但可以殊途同歸。法典化道路并不是法律現代化的唯一道路,英美法系國家就沒有民法典。不同的思維范式是各國法律文化的產物。在法律適用的邏輯結構中,法律規范是大前提。大陸法系的法律思維范式是演繹推理,法律規范通過成文法中法律條文明確表現出來。而英美法系的思維范式是歸納推理,法律規范需要從先例中歸納。大陸法系以法典為核心,嚴格解釋和適用法律。而以《美國法典》為代表的英美法系法典與大陸法系的法典具有不同的文化內涵。英美法系的法典是對判例法進行系統整理的產物,一部法典頒布以后,以前的判例法仍然有效,法典的效力取決于法官的選擇,只有在法官加以適用時法典才成為真正的法律。“法典的真正功能,正如今天的法學家所認識到的,并非僅僅是使過去法律發展的成果加上一個更美的和更權威的外形,而更多的是為了法學的和司法的更高更新的起點提供一個基礎。”
與大陸法系相比,英美法系具有催生環境權的法律文化環境,因為大陸法系的民法文化難以詮釋環境權的精神本質,而英美法系國家財產法中的信托制度有利于環境權觀念和制度的形成。環境權是一種限制其他權利濫用的權利,《法國民法典》確立的所有權絕對原則與環境權理論依據是矛盾的。《德國民法典》雖然出現了所有權社會化的趨勢,但由于局限于公私法的區分,環境權在民法典中難以定位,只能將它作為一種沒有類型化的人權,其理論論證也就比較模糊。美國學者薩克斯認為以公共信托為理論依據,系統論證了環境權的法律性質,為公民主張權利和政府進行環境管理奠定理論基礎。[2]美國在1948年制定了《水污染防治法》、1955年制定了《大氣污染控制法》、1965年制定了《固體廢物處理法》等單項法律,這些制定法在適用中優先于判例法形成的財產法。1969年美國制定了《國家環境政策法》,以之作為環境基本法來整合各單項法律,從而進一步提高了環境法的地位。與大陸法系環境基本法的地位相比,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在美國環境法體系中的地位具有特殊性。就其性質而言,它是一部從宏觀方面調整國家基本政策的法律,它對一切聯邦行政機關補充了保護環境的法律義務和責任,以統一的國家環境政策、目標和程序改變了行政機關在環境保護問題上的各行其是、消極渙散的局面。就其作用而言,它規定的環境影響評價程序迫使行政機關把對環境價值的考慮納入決策過程,改變了行政機關忽視環境價值的行政決策方式。它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為行政機關正確對待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兩方面的利益和目標創造了內部和外部的條件。由于《國家環境政策法》的特殊性質和作用,同其他的環境法律相比,它在美國環境法體系中顯然處于更高的位置o【3]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不僅體現了環境權觀念,它還規定了具體的環境權利制度,如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指導著各州的環境立法和環境規劃,以及具體項目建設。可不管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法律的內在精神許多方面是一致的。反映在環境法治方面,大陸法系是需要協調環境法與民法的關系,英美法系是需要協調環境制定法與判例財產法的關系。
在環境法律移植方面,不管是形式還是內容,兩大法系中對中國有利的觀念和制度就應吸收。中國有《環境保護法》,民法中的合同法、物權法、繼承法都有了,還加上一部侵權行為法,民法典的內容也就全了。可以
說,在注重形式方面,中國人并不差于外國人,能力似乎更強。所以,法律移植還應該注意“水土不服”的問題,尤其是法律文化中深層的民族精神在不同的法律體系中是不同的,法律移植不是照抄照搬,還存在“存異”的問題。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精髓可以為當代法律文化所繼承。從西周開始,封建統治者以宗法制為紐帶,通過禮、法調整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強化了人們對土地、宗族的認同和依戀感,這種傳統文化有許多不適應現代化的進程,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其作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西方法律文化的主要區別是:中國重視“和諧”,西方重視“私權”;中國人重視情感方面的禮儀程序,西方人重視理性方面的程序規則。不論是大陸法系的民法,還是英美法系的財產法,它們都是以私權神圣為原則,以人類的普遍理性為依據的“萬民法”或“普通法”,土地、水、礦藏等資源是與主體“人”相對的客體。而在中國,天人合一的權利觀念促成了對土地等資源母親般的依戀和熱愛,他們不愿離開故土,即使在海外謀生也希望葉落歸根,與西方人敢于殖民開拓、四海為家的海洋文化不同。在中國法律近代化過程中,法律移植所面臨的主要困難就是這種文化沖突。反對民法典的人認為,民法出、禮教亡;持“法典化觀點”的人看來,在刑法現代化過程,也經歷了同樣的問題。20世紀初,清廷按照西方刑法制定的《大清新刑律》中有一個罪名決斗罪,在《大清刑律草案》征求各級官吏的意見時,兩廣總督張人駿認為:“查中國閩粵江楚等省,只有聚眾斗械而無兩人決斗之事。既屬歐洲盛行,自難保中國之民不無仿效,著為定律,未嘗不可。然械斗乃現時所有,似未便不言械斗而專言決斗,仍宜明定械斗專條以警悍俗”0【1]修正案沒有采納他的意見,仍然保留了決斗罪而無械斗罪。現實情況是決斗罪沒有發生,而械斗、打群架倒是屢見不鮮。中國人之間如果有什么情感糾紛,不是通過決斗而是通過宗族械斗來解決。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決斗講究正當程序,這像兒戲一般可笑。
我國法學理論界有一種時尚,即喜歡討論民法法典化、環境基本法的法典化等問題,常忽視立法背后法律文化的考量。筆者認為,既然法典化是中華法律文化的傳統,中國環境立法的首要問題不是法律形式的改變,而是法律的可操作性與實效問題。法律形式的不同是容易統一的,法律移能否成功,最大的困難是不同觀念法律文化的磨合與協調。中國環境法走向世界過程中,主要的經驗和教訓就是如何揚棄中國傳統文化。我國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躍進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盲目推行毀林毀草開荒、圍湖圍海造田和打虎滅雀等征服大自然的運動,在“人定勝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等唯意志論的支配下,搞什么“開荒開到山頂,種田種到湖底”和“大煉鋼鐵”,結果造成了植被覆蓋率降低、水土流失嚴重、生物多樣性銳減、環境污染加劇、生態環境惡化、自然災害頻繁等一系列嚴重后果。近幾十年來,盡管黨和國家采取了一系列保護生態環境、保護野生動植物的措施,退田還林還草,治沙治水治山,但由于欠賬過多、積重難返、治理污染艱難和恢復生態緩慢,至今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惡化的趨勢。實踐和教訓使人們認識到,誰違背大自然的規律誰就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自然生態失衡即生態平衡受到破壞的根本原因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只有正確處理和協調好人與自然的關系,遵循自然生態規律,才能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2]改革開放后,對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繼承和外國先進文化的移植又成為中華法系發展的主題。
對國外先進的法律制度的移植,要與本國的本土資源相適應。在環境法的移植中,我們不能“得形忘義”。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權利觀在新時代背景中仍有其積極價值,環境法要具有權威性和可操作性,環境權觀念和制度就應該能夠為人們普遍接受和信仰,中國當代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在《中國人的道德前景》一書說:“我國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說明了市場經濟必須有法治作保證。這一點幾乎已被一切人所接受。但法治是否要道德的支持似乎還存在著爭議。依我看來,道德是法治的基礎,如果沒有道德的支撐,法治并不能獨立地支撐市場。”[1]以“天人合一”的權利觀為指導思想,中國傳統文化重視血脈親情、孝道、誠信,這些對當代中國環境法治建設仍有影響。中國恢復了清明節、重陽節等傳統節假日,這有利于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現階段我國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就是讓“樹定根、人定心”;農村土地承包權的改革,也是為喚起農民對自己生活土地的熱愛。在封建社會,一些家族通過編制族譜,立宗祠,促成了子子孫孫對土地母親般熱愛的情結。在現代社會,雖然族譜中的“身份”制度不利于土地流轉和市場經濟發展,但應當肯定的族譜中仍有許多對現代文明建設起積極作用的某些倫理道德規范,如敬長老、孝父母、尊師長、友兄弟、睦近鄰、崇儉樸、戒奢侈、禁賭博等。這些倫理道德規范對當代環境觀念和制度建設仍有重要價值,環境立法應以這些文化規范和客觀法作為立法平臺,貼近生活世界,這樣才能使公民樹立環境權利觀念和對環境法的信仰,環境法也才具有可操作性。
摘自:余俊著《環境權的文化之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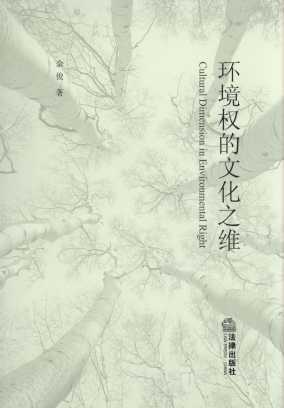 求同存異的法移植
求同存異的法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