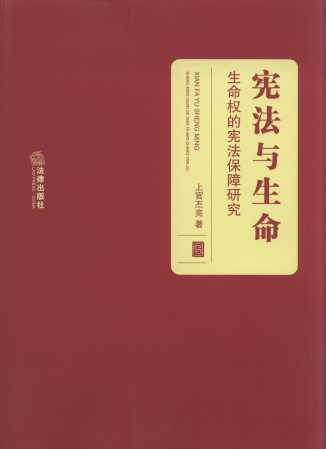
憲法保障的獨特價值——審查依據、立法依據、解釋依據
憲法保障生命權可防御和對抗國家權力的侵害,然而行政法、刑法、訴訟法等公法對生命權的保護同樣具有防御和對抗國家權力的功能。行政法規定行政機關及工作人員保護生命權的職責和對侵害生命權行為的行政制裁以及刑法規定對侵害生命權行為的刑事制裁、訴訟法對保護生命權的程序規定等,顯然直接或間接地限制了行政權和司法權,防御著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侵害。⑤前面只是證明,保護生命權僅僅依靠民法是不夠的,但在實際上各國往往還有行政法、①刑法、(訴訟法③等其他部門法對生命權的保護。毫無疑問,到此尚未徹底回答憲法保障生命權的必要性。筆者認為,憲法保障生命權具有監督審查部門法對生命權的保護是否違憲的獨特價值,這是生命權必須有憲法保障的關鍵所在。
憲法的監督價值來源于憲法至上的最高法觀念,而憲法是最高法的觀念又來自英國的高級法思想和實踐,特別是英國著名法官和法學家愛德華·柯克爵士(Si,’Edward Coke)的高級法思想,最后由美國人首先在憲法中規定下來。
在1215年英國國王約翰與男爵們簽署了《大憲章》(史稱《自由大憲章》),特別是1225年第二次頒布《自由大憲章》之后,《大憲章》有一個世紀的輝煌時期。在此期間,國王愛德華一世于1297年頒布《憲章確認書》,命令所有的“法官、郡長、市長和其他大臣,凡是由我們任命且聽命于我們的執掌王國法律的人”,都要在他們處理的所有訴訟中,將《大憲章》當作普通法來對待,而且只要與《大憲章》相矛盾,任何審判都要宣布為無效。在愛德華三世統治時期,《大憲章》作為高級法的思想達到了最高峰。在愛德華三世統治接近晚期的1368年,還頒布法律明確宣示:任何成文法的通過,如與《大憲章》相悖,則必然是無效的。但到了都驛王朝(1457~1603)專制統治時期,《大憲章》陷入了無人問津的境地。17世紀初,在都驛王朝壽終正寢而斯圖亞特王朝立足未穩之際,英國人開展了限制王權的運動,《大憲章》開始復興,其中柯克起了很大的作用。1610年,當時擔任高等民事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柯克在裁判Dr.Bonham’s案所寫的“附論”中提出:“在許多情況下,普通法會審查議會的法令,有時會裁定這些法令完全無效,因為當一項議會的法令有悖于共同權利和理性、或自相矛盾、或不能實施時,普通法將對其予以審查并裁定該法令無效,這種理論在我們的書本里隨處可見。”柯克所說的“共同權利和理性”是某種永恒不變的、最基本的東西,它就是高級法。柯克認為《大憲章》之所以被稱作“大憲章,并不是由于它篇幅巨大……而是由于……它所包含的內容至關重要且崇高偉大,簡而言之,它是整個王國所有的基本法律的源泉”。他重申,任何與《大憲章》相悖的法律和判決“皆為無效”。④然而,柯克關于普通法監督議會的行為并可宣布無效的主張,因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確立了“議會至上”原則而落空,卻在美國得以實現。②
“在美洲殖民地紛紛建立之時,與柯克和洛克的名字連在一起的高級法學說在英國的影響已達到了高潮”,柯克“他的理論先于洛克的而傳播到美洲殖民地”。美國早期的律師和法官在處理案件時往往都引用柯克的著作《法律報告》或《英國法總論》中的觀點,柯克在Bonharn’s案中提出的觀點不斷被人引證。1761年波士頓
的青年律師奧提斯(又譯為奧蒂斯或奧迪斯)在Writs of Assistance案中對法院頒發的協助英國政府實施貿易與航海條例的一般搜查令進行抨擊時引用柯克在Bonham’s案中提出的觀點作為法理依據,按美國革命領導人之一亞當斯的概括,奧提斯在案件辯論中提出:“就議會的法令而言,違背憲法的法令無效,違背自然公平的法令無效,而且如果議會的法令以請愿書所采用的言詞來制定,那也將是無效的。執行法院必須廢止使用這樣的法令。”幾年后,亞當斯本人(他也是律師)在針對馬薩諸塞總督和議事會而提起的訴訟中,就利用奧提斯的觀點反對《印花稅條例》,而弗吉尼亞縣法院也宣布有關議案無效。有關該案的報告是這樣寫的:“所有的法官都一致同意這樣的觀點:‘只要他們認為所公布的法令是違背憲法的’,那么該法令就不能約束或影響弗吉尼亞的居民,就與這些居民毫無關系。”1’768年《馬薩諸塞通訊》這樣寫道:“在所在自由的國家中,憲法是確定的,由于最高立法機關的權力和權威皆源于憲法,所以它不能擺脫憲法的限制,否則便會破壞自由賴以存在的基礎。”③后來,美國人將高級法、最高法的觀念寫入了《美國憲法》。1787年《美國憲法》第6條第2款明確規定:“本憲法,依照本憲法制定之合眾國法律及經合眾國授權已經締結或將來締結之條約,均為本國之最高法;且不論任何州憲法或法律內容對之有何抵觸,各州法官均受其約束。”聯邦黨人漢密爾頓等人為爭取各州批準美國憲法而發表文章,明確強調憲法在法律之上的最高法地位:“代議機關的立法如違反委任其行使代議權的根本法當歸于無效乃十分明確的一條原則。因此,違憲的立法自然不能使之生效。如否認此理,則無異于說:代表的地位反高于所代表的主體,仆役反高于主人,人民的代表反高于人民本身。”“如果二者間出現不可調和的分歧,自以效力及作用較大之法為準。亦即憲法與法律相較,以憲法為準;人民與其代表相較,以人民的意志為準。”①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馬歇爾在1803年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中重申:“一個與憲法相抵觸的法案是否能成為國家的法律?……在這兩種選擇中,沒有中間道路可走:憲法要么是一種優先的、至高無上的法律,不能被一般法案修改;要么與一般法案處于同一層次,并與其他法律一樣,立法機關可以隨時加以修改。如果前種方式是正確的,那么與憲法相抵觸的立法法案就不是法律;如果后種方式是正確的,那么成文憲法以人民的名義限制這種本質上無法限制的權力則只能成為一種荒謬的企圖。顯然,那么成文憲法的制定者們將憲法視為國家基礎的、重要的法律,這種政府所堅持的理論是:與憲法相抵觸的立法法案都是無效的。”②在論證憲法至上的基礎上,馬歇爾創立了美國的司法性違憲審查制度。正如美國著名憲法史學家愛德華·s.考文所指出:“既具備制定法的形式,又以司法審查制度作為補充,高級法又恢復了它的青春活力,從而進入了其歷史上的一個偉大時代,這是從查士丁尼時代以來法學上最富有成果的時代。”⑨自美國確立憲法至上的高級法原則和違憲審查的制度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在憲法上規定憲法的最高法地位,明確規定法律不得與憲法相抵觸,違憲者無效,并且建立起違憲審查制度。
正因為憲法是高級法、最高法,憲法具有至上性,所以憲法規定基本權利,意味著憲法基本權利約束普通法律以及有關國家機關,正如前面已經提及的,麥迪遜提出憲法修正案《權利法案》建議時明確指出,《權利法案》的目的是“對立法機關加以防范”并防止行政官員濫用職權。1949年《德國基本法》第1條第3項則更明確地規定:“下列基本權利應作為可直接實施的法律,直接約束立法、行政和司法機關。”同時,憲法規定基本權利,意味著憲法為有權機關監督和審查普通法律有關基本權利的規定以及國家機關有關保護和限制基本權利的行為是否違反憲法基本權利的規定提供了依據和標準。正如林來梵教授所言:“與其說憲法的存在是為了給各種立法提供立法基礎,倒不如說是為了審查各種立法提供規范依據。這也說明了,憲法作為最高法律規范的意義,主要并不體現在它是一個‘授權規范”’。④
由此可見,憲法規定生命權,主要是為監督審查普通法律對生命權的規定以及國家機關有關保護和限制生命權的行為是否違憲提供依據和標準。憲法保障生命權,就意味著對有關生命權的法律和行為進行違憲審查,它不僅能像一般公法那樣防御公權力對生命權的侵害,而且它能防御立法權對生命權的侵害。正如德國哥廷根大學公法教授c¨stian starck所說,“憲法保護基本權利之旨趣,隱含有一種內在的邏輯,亦即對于基本權利之保護,尚應包括防范來自立法者之侵害”,為此美國和歐洲各國先后建立起“審查法律是否合乎憲法之意旨,尤其是審查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權利之旨趣”的違憲審查制度。④這種由憲法的至上性產生的憲法對國家立法行為的監督價值(標準價值,它是違憲審查的標準,也是生命權保護的最終衡量標準),可以說這是憲法保護的獨特價值,這是行政法、刑法、訴訟法等一般公法保護所不具備的價值,這也是生命權非有憲法保障不可的根本原因所在。
當然,憲法規定生命權,生命權成為一項基本權利,可以為立法機關制定有關生命權保護和限制的普通法律提供立法依據,立法機關在制定相關法律時至少應考慮不得同憲法上有關生命權的規定相抵觸。
此外,憲法上的生命權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別價值和作用——它是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執行和適用有關生命權的法律時的解釋依據。這一點在我國長期以來被忽視,應當引起重視。執行和適用法律,不得不理解和解釋法律,而法律是依據憲法而制定的,立法機關在立法時至少考慮了不與憲法相抵觸,所以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在執行和適用法律中理解、解釋和適用法律時也應考慮憲法,應當考慮我們對法律的理解和解釋是否符合憲法的基本精神、是否與憲法相抵觸,依照憲法來解釋法律,讓所適用的法律不違背并包含憲法精神。由此看來,憲法上的生命權可以而且應當成為普通法律有關生命權條款的解釋依據。
綜上所述,完整地講,生命權人憲不僅可以防御公權力特別是立法權對生命權的侵害,為生命權的保護提供違憲審查的依據,而且可以為生命權的保護提供立法依據和解釋依據,憲法上的生命權是生命權保護的審查依據、立法依據和解釋依據,這就是生命權成為基本權利的特別價值和根本原因。
摘自:上官丕亮著《憲法與生命:生命權的憲法保障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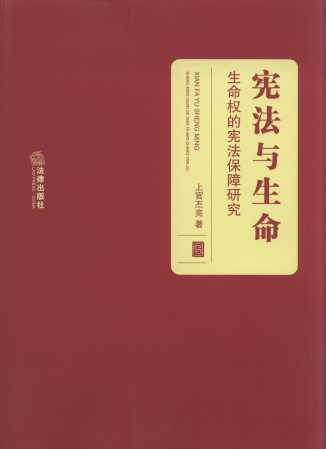 憲法保障的獨特價值——審查依據、立法依據、解釋依據
憲法保障的獨特價值——審查依據、立法依據、解釋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