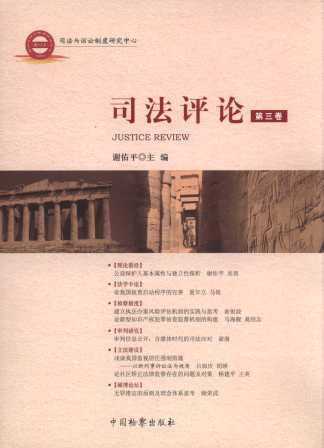
自媒體時代的審判信息公開
自媒體時代的審判信息公開模式可以區分為主動公開與被動公開兩類。審判信息的主動公開是指人民法院依職權公布官方審判信息,除傳統的公民旁聽庭審、接受新聞媒體監督之外,還包括庭審直播、裁判文書上網等信息化手段。而審判信息被動公開則是指非官方的個人或機構發布未經認證的審判信息,一般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
(一)審判信息的主動公開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一系列促進司法公開的文件中都體現了審判信息主動公開的精神,《關于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第2條規定:“對于社會關注的案件和法院工作的重大舉措以及按照有關規定應當向社會公開的其他信息,人民法院應當通過新聞發布會、記者招待會、新聞通稿、法院公報、互聯網站等形式向新聞媒體及時發布相關信息。”《關于人民法院直播錄播庭審活動的規定》第2條第1款規定:“人民法院可以選擇公眾關注度較高、社會影響較大、具有法制宣傳教育意義的公開審理的案件進行庭審直播、錄播。”《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以下簡稱《裁判文書規定》)第1條規定:“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應當遵循依法、及時、規范的原則。”為了貫徹落實以上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還在2010年10月印發了《關于確定司法公開示范法院的決定》,將100個法院選為“司法公開示范法院”①,并制定《司法公開示范法院標準》,明確量化考核標準。②
遺憾的是,一系列規范性文件出臺并未有效實現“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的工作目標,司法公開依舊進退維谷。在處理某些“公案”的過程中,人民法院向媒體和公眾發布的審判信息和評論甚至激化了社會矛盾。最為典型的即是李昌奎案,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田成有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社會需要更理智一些,絕不能以一種公眾狂歡式的方法來判處一個人死刑,這是對法律的玷污。”“10年之后再看這個案子,也許很多人就會有新的想法。”③此番言論非但沒有平息輿論質疑,反倒產生了“火上澆油”的效果,使案件再掀波瀾。進入21世紀以來,越來越多國家的法院向攝像機敞開大門,即便是相對保守的英美最高法院也不例外。④庭審直播有益于民主,能讓更多普通百姓了解司法,我國法院在對庭審進行電視直播的同時,也正嘗試微博圖文直播的方式,以自媒體為平臺,輻射范圍更廣。但直播與否并不能成為衡量司法透明度的標桿,一些地方法院為了保證庭審“順利”進行而先判后審,直播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義。至于裁判文書上網,《裁判文書規定》第2條規定“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書可以在互聯網公布”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具有法律適用指導意義的生效裁判文書應當在互聯網公布”,不難看出,裁判文書并非“應當”公布,也無須全部公布。⑤此外,《裁判文書規定》第8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全國統一的裁判文書網站。”筆者特意登錄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官方網站,在“權威發布”的“裁判文書”一欄中,最近一次更新為2010年12月31日,即便最高人民法院只需要公布具有法律適用指導意義的生效裁判文書,但近一年半的時間里都沒有出現所謂“具有法律適用指導意義”的案件,未免讓人有些失望,審判信息的主動公開還僅僅停留在紙面上,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貫徹落實。
(二)審判信息的被動公開
審判信息的被動公開與審判信息的主動公開相對應,在一些“公案”中,司法機關未能及時公布相關信息,即會出現所謂“知情人士”披露“內部消息”,這一特點在自媒體發達的今日尤為顯著。自媒體具備平民化、個性化、傳播迅速等特點,發布信息并不需要相應的資質認定,一些可信度不高的信息經“意見領袖”轉發、評論之后即可引發共鳴,個體意見與群體意見經過自媒體的有效融合,克服個體表達的分散性,凝結成輿論壓力。特別是與司法相關的信息,形成公眾、媒體、為政者與司法官的四方角力,架構“輿論法庭”,通過輿論和民意影響司法裁判。從應然的理論上講,輿論法庭會對陪審團產生影響,但很難對沒有陪審團制度的司法活動起影響作用,因為司法機關是獨立行使職權的,并且法官的職業習慣往往對民意和輿論抱排斥態度。民意和輿論即使有影響,也是在法院不知不覺狀態下產生的。但是如果通過為政者,則毋庸置疑可以直接干預司法,輿論法庭之于我國司法的影響,正是通過為政者而產生的。①司法的合理化要求法院不受來自外界的影響,只根據證據和規范進行精密的分析、推理以及裁量,以確保法律標準在理解和執行上的統合,避免一人一是非、一事一立法的混亂,避免審判機關在政治力學的干預下搖擺不定。然而,司法合理化的進程在中國遭遇到制度和文化的“瓶頸”。審判不能獨立于政府權力以及司法腐敗的現實,導致人們訴諸輿論監督,尤其是弱勢群體特別需要獲取輿論的支持以實現某種程度的力量均衡。藥家鑫案中關于“富二代”、“官二代”的風影傳說以及被害人親屬把“不判死刑不葬妻”作為談判手段的事實,都證明了這一點。②審判信息的被動公開是在官方信息缺位的前提下,公眾基于質樸的利益訴求而形成的無奈之舉,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監督司法的作用,但“自媒體”信息畢竟不是官方發布,缺乏官方信息必然為謠言滋生供給土壤,造成公眾與司法機關信息不對稱,影響司法公信力,有礙社會穩定。
摘自:謝佑平 主編 《司法評論(第3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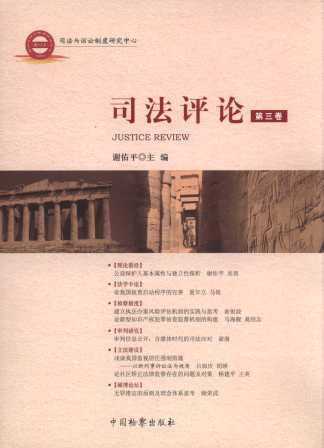 自媒體時代的審判信息公開
自媒體時代的審判信息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