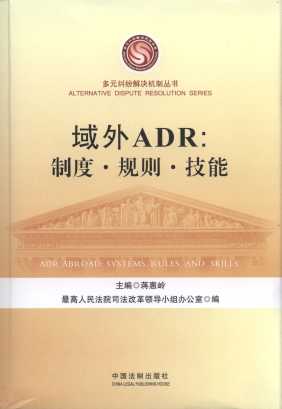
調解能否成為一個真正的職業
原作/邁克爾·麥克愛爾拉斯 翻譯/代秋影①
隨著時間的更迭,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超越了生物界的范疇,“自然選擇”的很多變種理論已經被廣泛地用來解釋文化、社會、企業、科技如何產生和發展等問題。同樣,隨著世界大環境的變化,達爾文的進化論也被應用到了糾紛解決問題中。最近,我有幸采訪了文化傳記作家羅伯特·卡內羅,他是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南美動物行為學分館(紐約)館長。他向我敘述了不同時期在亞馬遜流域與不同的部落人民生活的奇聞異事,包括那些部落奇特的糾紛解決方法。他說,通過諸如手持棍棒,打架比輸贏的原始野蠻方式解決爭端,在50至100人的部落里很盛行,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可能不會讓所有人滿意,那些不滿意的人只能黯然離場。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擴張,事情越發復雜,靠打架解決爭端的方式已經成為歷史。迄今為止,所有的較大的社會群體都有了正式的糾紛解決方法(通過司法、正式、官方的方式)。
北美、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地具有適合調解產生和發展優厚的“生態條件”,故而調解制度在上述地區非常“繁榮”。現在的問題是,調解制度在其他地區可否“健康發展”?調解能否解決跨境糾紛?在上述地區所有有過調解經驗的人都會認為,調解制度非常有潛力發展壯大為世界上不同經濟制度和區域間糾紛的主要解決方式,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調解制度發展過程中會遇到的障礙和挑戰。
調解制度的淵源
調解制度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國的儒家文化,中東和非洲地區也出現過調解的影子,但是,現代意義上“調解”制度的概念則是由哈佛大學桑德爾(F'rank Sander)教授應時任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伯格邀請,在1976年龐德學術會議的演講中首次提出的。這次大會將那些對美國司法制度不滿的學者和實務人士聚集在一起,其中桑德爾教授題為“司法制度的展望”的演講引發了一場關于司法制度根本變革的思考。
前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康納曾說:“法院不能成為解決爭端首先考慮的地方,而應該是解決糾紛的最后途經,即通過所有其他替代糾紛解決方式都不能解決時,才由法院解決。”所以,現代的“調解”制度僅僅有30多年的歷史。在加利福尼亞州,縱然調解制度適用廣泛,但也稱不上成熟,只有那些已經發展了數百年的職業(醫療或與法律有關的職業)可以稱為“成熟”。在北美、英國和荷蘭,調解制度已經取得了一席之地,但在其他的地區,調解制度可能鮮為人知,并且時常被誤解,缺乏尊重和認可。
在一些地區,有一種很奇怪的現象:調解制度剛剛起步發展,但是由于調解員過多,卻出現了慢性的飽和。有過調解經歷的人都認為,出現這一問題的關鍵不在調解制度本身,而是調解的宣傳和展現方式。
以英國為例,在掌握了調解的初始技術并得到美國的相關指導之下,英國現在擁有數千名受過培訓的調解員,但其中只有20個是專職的。全國的50名調解員解決了全國約80%的調解案件,而其他數千名調解員很難有機會獲得調解經驗和調解技能。即便是這種狀況,英國還經常被稱為“具有成熟調解制度”的國家。
調解制度的發展就像正在醞釀的暴風雨,必定勢不可擋。一些前任或者現任公司法務顧問也認同這個觀點。在他們看來,在經濟混亂、信息技術蓬勃發展和公司法務顧問缺位三個要素的聯合交錯作用下,傳統訴訟參與者的角色正在轉變,他們不再只是被動地處理糾紛,而是逐漸演化為主動的爭端解決者,或稱為“結局促成者”。另外,考慮到調解在一些地區良好發展的現狀,其必定有發展為全球化糾紛解決制度的可能,但是,現在的問題是,調解領域的“從業者”(調解員和其他提供調解服務的人員)能否有效的應對,使上述“可能”變為現實呢?
坦誠地說,調解成為全球性的制度亟須訓練有素的、能力過硬的調解員(無論其專業背景如何);即便如此,爭議的當事方也需要主動地把調解當做一種解決爭端的方法,而不是排斥它,因為當事人通常認為如果調解員素質不高、能力不強,調解的結果也不會好。
調解——轉變中的制度
為調解制度發展奔走呼吁最急切的人莫過于我們這些負責解決糾紛的人了,因為我們直接經歷過很多無法化解的糾紛。有很多人將調解看成一種解決爭端的“高級”方式,但是為什么調解就是不能在世界范圍內推廣開來呢?有很多因素阻礙調解的快速發展。
一個因素是費用。在北美、英國和澳大利亞,由于訴訟費用昂貴,人們就選擇了費用相對較低的調解,但是,在其他地方可能不是這樣,比如意大利,那里的訴訟費用就很低廉。
另一個因素是效率。眾所周知,美國法院極低的效率也使得當事人被迫選擇耗時較短、效率較高的調解。故而,法院的低效率為調解制度的繁榮提供了“沃土”,但是,意大利司法系統的效率本來就非常高,甚至有一些國家(諸如印度)還將意大利當成榜樣。誠然,意大利也采取措施以促進調解的發展,比如立法規定了某些糾紛的強制調解,但是收效甚微。
各國調解質量的參差不齊阻礙了調解的發展。只有高質量的調解結果、透明的程序和可靠的信譽才能使調解真正被人接受為一種“職業”。
還有一個阻撓調解全球發展進程的障礙,那就是“調解力量零零散散,難以形成合力”。不同的地區也不乏先進的調解發展新思路,但顯得比較分散,沒有進行整合。印度仲裁和調解理事會正在極力敦促印度調解事業的發展,但總的說來,分散的努力很難單獨取得成效。當然,國際上也經常舉辦有教育意義的調解經驗交流活動,但遺憾的是,這種交流和分享只是在相對較小的區域內展開,到現在還缺乏全球性的交流和分享平臺。
上述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礙了調解制度的發展。我曾與前任英美煙草知識產權負責人、現任國際調解學會執行主任李德斯談論過會有多少爭議當事人有調解意向而最終進入調解,我說可能是十到二十分之一,但他認為這個比例可能更低,大約為五十分之一。我們兩人都深信高質量的調解結果不會讓那些選擇調解作為解決爭端的人后悔,我們也驚訝于這個事實——讓對方當事人接受調解是多么困難。
國際調解學會的使命
國際調解學會是2007年組建的一個具有慈善性質的非營利組織,總部在荷蘭的海牙。學會的任務是舉辦會議、鼓勵公眾適用調解解決爭端、解釋調解相關問題、簡化調解程序,促進調解標準的透明,提高調解工作的標準,以推進調解制度的發展。為了實現上述使命,學會號召調解領域的所有人以及關心和支持調解事業的人要團結協作,把國際調解學會看成一種機遇,一個載體。只要共同努力,調解制度就會在各國和世界范圍內良好地“運轉”。我也呼吁那些經驗豐富的調解員能夠盡快加入國際調解學會,成為其中一分子,為調解制度的發展和高效運行交流和分享他們的經驗和想法。政府和其他捐贈者們也要在經濟上積極支持,使學會有能力舉辦更多的活動。
現代調解制度的歷史不過30年,但它已經對訴訟的昂貴性和復雜性提出了挑戰。調解已經可以很好地適應不同的法制環境,甚至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專門的職業。當前,我們的任務就是盡最大努力,將調解制度建設成為一種更加獨立的、可信的、能夠與傳統訴訟制度相較高下的一種基本的糾紛解決機制。
摘自:最高院司法改革辦 《域外ADR:制度.規則.技能/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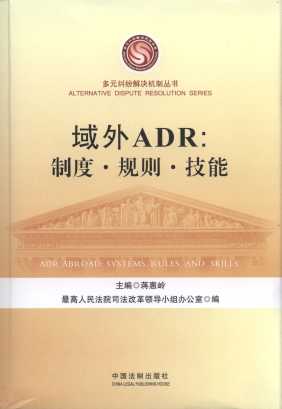 調解能否成為一個真正的職業
調解能否成為一個真正的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