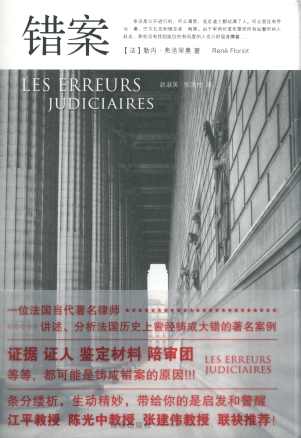
司法人員應具有理性的懷疑精神
隨著近些年來媒體披露的佘祥林案、趙作海案等震驚社會,錯案成為了司法界檢討和全社會矚目的對象,這本書顯然很有意義。我期待讀者在閱讀本書之后,能夠提升對于錯案的警惕和對司法公正的關注,尤其是培養一種理性的懷疑精神。對于司法人員來說,尤其如此
張建偉
想必您也有過這樣的閱讀經驗:看到一本書先是被書名吸引,隨手拿起來翻翻,覺得略有些意思,買回去讀,讀的時候真覺津津有味;后來閑暇時又讀過幾次,越發覺得這是一本值得花費時間好好讀一讀的書,甚至不知何時心里恍若存了一份不離不棄的眷戀。想當初書店里不經意的一瞥,竟在日后結了一段緣,不禁自矜慧眼獨具、心有靈犀。我當初邂逅《錯案》一書,便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并體驗到這樣的感受。
每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這本書的作者是法國著名律師勒內·弗洛里奧。他基于豐富的辯護經驗,抱有對司法錯案受害人的悲憫情懷,寫成了這本聚焦于錯案的書。讀者不難體會到,雖然作者無意煽情,字里行間卻時時讓人感受到有所觸動、幾分感動。
在作者為本書寫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值得反復玩味:“請不要以為您是一位行為端正的好父親、好丈夫、好公民,就一輩子不會與當地的法官打交道。實際上,即使是最誠實、最受尊重的人,也有可能成為司法部門的受害者。”“不要以為您的聲譽、您工作上的成績和社會關系可以保護您。您如果以為這種司法裁判的錯誤只會被那些地位低下和倒霉的人碰上,那就大錯特錯了。這種錯誤不分青紅皂白地打擊著各種人,既有權貴,也有平民。”這些話包含的意思,我稱之為“涉訟人假設”——對于被指控為罪犯的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保護,不能僅僅看作是對社會一極小部分人群的特殊保護,而應將其放在更宏大的視野里,視為對整個社會中所有成員的保障,這是因為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可能成為司法的受害者。道理很簡單,“公正的審判是不容易的事情。許多外界因素會欺騙那些最認真、最審慎的法官。不確切的資料、可疑的證據、假證人以及得出了錯誤結論的鑒定等都可能導致對無辜者判刑。”
弗洛里奧在書中用了較多筆墨介紹德萊福斯案件的來龍去脈。德萊福斯案件之鑄成,本來出于錯誤的判斷,但在新的證據和事實逐漸顯露該案件可能是冤錯案件的時候,大權在握的人刻意去掩蓋這是一起冤錯案件的行為更令人恐懼。這可能會令讀者意識到:國家、政府、軍隊高層以及與之聯系的權力,都可以成為錯案的形成因素,甚至在鑄成錯案中發揮關鍵作用。當國家權力或者政府權力有意炮制冤錯案件或者刻意掩蓋已經鑄成的冤錯案件的時候,他們在社會上的那種虛幻的神圣色彩也隨之褪去。從這類案件中,我們應當獲得的一個基本認識是,國家、政府這些抽象而神圣的名詞掩蓋了組成國家、政府的那些人是和其他人一樣都是普通人而不是天使。既然如此,就應當像約束凡夫俗子一樣去約束那些握有大權的權貴。當構成政府的人是一群政治流氓、無賴的時候,當政府權力被恣意濫用的時候,其神圣性就更被黑煙籠罩。
造成錯案的原因分析
在介紹諸多錯案之時,弗洛里奧逐一分析了造成錯案的原因,概括起來有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有些案件,有著確鑿的證據,但依這些證據作出的推理判斷是錯誤的,如此一來,案件就弄錯了。例如有些案件,究竟是正當防衛、故意殺人還是過失殺人容易形成誤判。尸體或者受傷的人擺在這里,致人死亡或者傷害的兇器也擺在這里,究竟屬于正當防衛還是殺人,同樣需要掌握進一步的證據。見到尸體或者受傷的人,就遽然斷定發生了殺人罪案,就可能冤枉了實施了正當防衛的人。在窩贓案件中涉及犯罪所得還是因輕信而取得,也很容易發生誤判。對于這類案件,進一步了解案情,掌握更多情況,才有可能避免將事物簡單歸因一致造成錯案。
其二,死因判斷錯誤也是常見致錯原因。弗洛里奧特別指出,無辜者被誤判并非罕見。他認為:法庭會給一個無辜者判刑,致錯原因之一是死因判斷錯誤。正常死亡中會有暴死的情況,遇到暴死時,人們容易疑竇叢生,以為有罪案發生,而且罪犯還逍遙法外,按這個思路追蹤下去,有的無辜者因此背上倒霉的黑鍋。
其三,法庭被被告欺騙。弗洛里奧指出:“經驗證明,各種人都有可能有意無意地欺騙法庭。”在各種人中,“首先是被告。罪犯為了逃避公正的制裁,常常想方設法把法庭引入歧途,法官們對這一點都是有所警惕的。罪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在法庭辯論時會毫不猶豫地提供一些偽造的證據材料,法官們對這一點也是十分清楚的。”令人感到驚訝的是,“也會發生這樣一種事情,即無辜的人向法庭‘承認’了他并沒有犯過的罪行。”因此,對嫌疑人的供詞不加懷疑,照單全收,就常常容易釀成裁判的錯誤。
其四,司法實踐中,法庭很可能被徹頭徹尾偽造的書證引入歧途。例如,偽造者模仿了別人的筆跡和簽名,甄別不清就可能導致誤判。
其五,如果不加警惕,誣告會發生誤導司法的作用,“一個虛構出來的‘受害者’去控告無辜者,司法部門往往把無辜者錯判。”例如,“一個未成年的男孩或女孩,常常說自己是那些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傷風敗俗的罪行的受害者。”審判人員必須自我提醒,不能盲目相信他們的陳述。
其六,假的證言和錯誤的證言可能會欺騙法官,使之作出錯誤裁判。在法國,“假證是大多數裁判錯誤的起因。”弗洛里奧告誡:對于偽證和錯證,司法人員有責任保持警惕。
其七,辨認錯誤是造成錯案的另一重要原因。辨認錯誤發生的原因之一是“圖像的重疊”,還有一種受公民責任感支配下的錯誤指認。
其八,司法鑒定在案件性質的判斷方面往往發揮著關鍵作用,正確的鑒定有助于促使案件真相大白,甚至鑒定本身就可以使案件真相大白,同樣,錯誤的鑒定將帶來嚴重后果。存在這樣的因果關系,鑒定錯了,裁判就會發生錯誤,這是肯定無疑的。
其九,前科資料、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證據容易造成法庭對被告人的偏見,從而造成誤判。弗洛里奧贊賞一些國家不讓陪審員了解被告在違反法律方面有過哪些經歷的做法。
其十,錯案也可能源于法官的疏忽。法官并非上帝,當然無法期望其全知全能。法院以裁判為根本職能,甚至有人認為判斷是司法權的本質特征。各種外界干擾因素會造成法官誤判,造成這種誤判的是各種客觀原因。不過,法官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會造成誤判,對于這種誤判情形,法官自身難辭其咎。
上述這些分析,對于我國司法人員辦理刑事案件都具有警醒和指導作用,對于可能導致錯案的各種風險,司法人員不能不高度警惕和嚴加防控。
作者的告誡大有裨益
令人感興趣的是,弗洛里奧特別提到,在法國這種法治成熟的社會,警察權力受到制約,使用暴力取證的方式已經不太多見,他指出:“只是極少數搞調查的人使用暴力,而且現在比過去更少見了。”暴力取證行為減少,對于減少錯案發生的可能性來說,無疑具有積極作用。不過,非法取證的方式不限于暴力,還包括威脅、引誘和欺騙等方式,這些取證方法同樣可能導致錯案。就誘供而言,“即使不用暴力,也能以許諾很快釋放的辦法,從某些嫌疑犯那里獲得口供。道理很簡單:警察說:‘如果你承認這并不嚴重的事實,我們就讓你走;反過來,你不承認的話,我們就要進行核實。那么,為了避免你干擾對質,我們就不得不把你拘留,直到把事情弄明白。’”采取這種辦法的警察,一般都相信他可以讓罪犯認罪,而無辜者會堅決否認。可是,經驗證明情況恰恰相反。對于某些被拘禁的人來說,釋放的許諾值得用虛假的認罪來兌現。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告誡對于我國司法人員可謂適逢其時。顯而易見,注重發現案件真實的我國立法和司法部門,對于刑訊以外很容易導致虛假陳述的威脅、利誘和欺騙等非法取證方法并沒有給予足夠重視,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沒有以鮮明的態度要求排除那些以利誘和欺騙方式取得的言詞證據。針對這種情形,讀讀《錯案》中弗洛里奧的告誡是大有必要的。
我最初讀到《錯案》一書是十幾年前的事了,那時在我國刑事司法領域中“錯案”尚未成為一個熱詞。即便如此,當時一卷在手已經感覺開卷大為有益,對于司法來說,無異于雪中送炭。如今隨著近些年來媒體披露的佘祥林案、趙作海案等震驚社會,錯案成為司法界檢討和全社會矚目的對象,這本書顯然更有意義。我期待讀者在閱讀本書之后,能夠提升對于錯案的警惕和對司法公正的關注,尤其是培養一種理性的懷疑精神。對于司法人員來說,尤其如此。
通讀本書,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作者身為律師的視角,這一視角對于防控錯案的發生不失為最佳角度之一。不過,書中自然流露出來的辯護立場,可能使其個別觀點不一定能夠遽然為司法人員所認同和欣然接受。一個典型的觀點是,作者期望裁判者對于被告人有罪只要內心存在些微的懷疑就應當勇于作出無罪判決。這對于防止發生錯案來說是相當有效的,但由于司法人員還肩負著通過司法裁判實現社會防衛和通過懲罰犯罪來伸張正義的職能,執槌司法的人們真的面對司法抉擇的時候,未必如紙面上寫的和期待的那么輕松。不過,即使如此,包含在本書旨意中的如下提醒是十分必要的:應當保持每一分警惕,防止無辜者被錯誤地定罪和判刑。
(本文為《錯案》序言)
摘自:(法)弗洛里奧 著 《錯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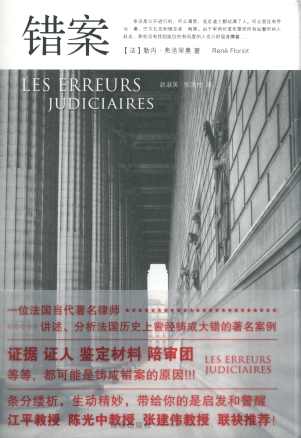 司法人員應具有理性的懷疑精神
司法人員應具有理性的懷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