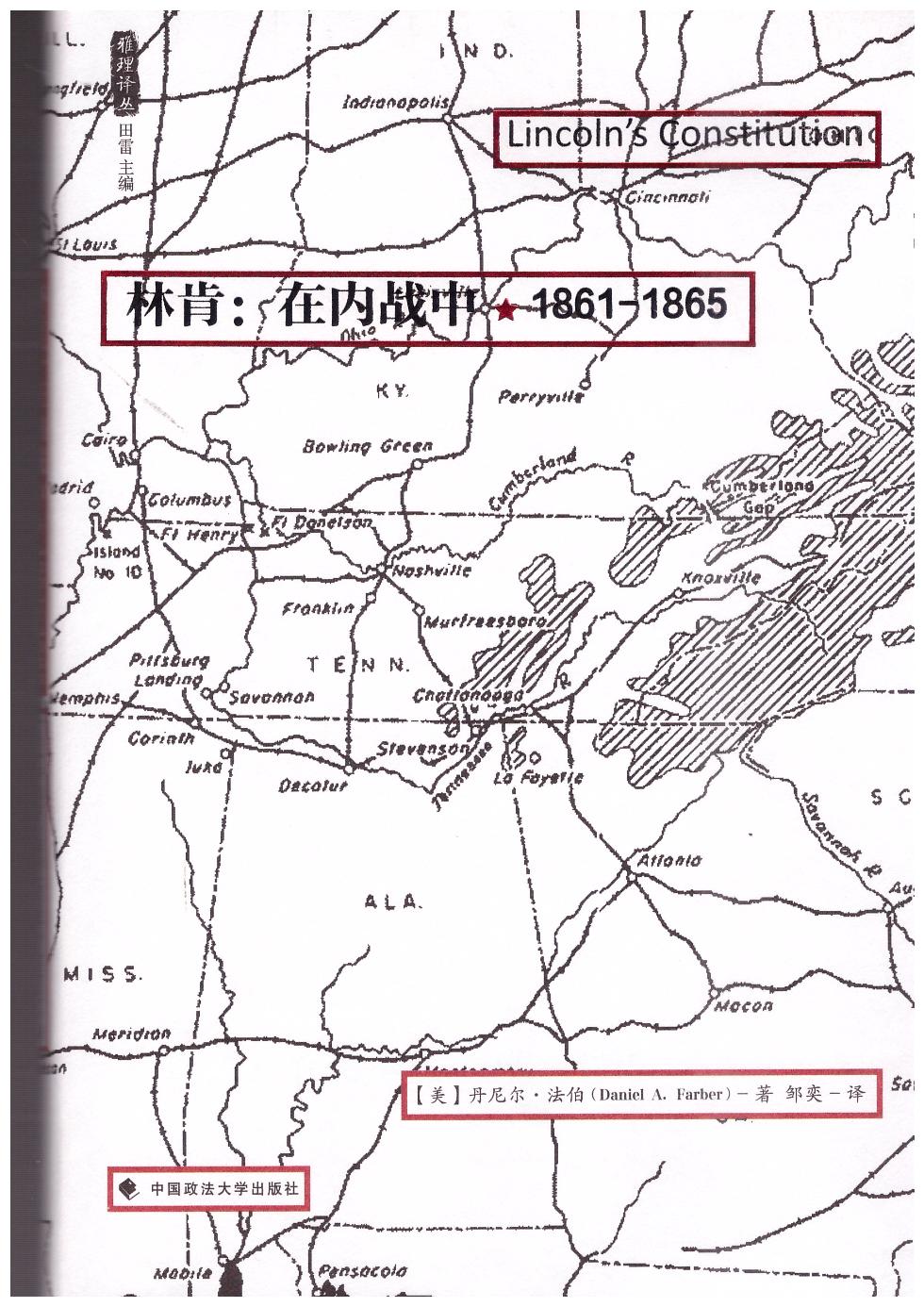
司法機關的回擊
當杰斐遜和麥迪遜將某種《憲法》解釋者的角色賦予各州時,聯邦法院日漸強調國家的最高地位。從1815至1825年這十年間,馬歇爾法院下達了幾個重要的判決。該法院的意見具有獨特的智識風格。正如一名主流的憲法史學家所闡述的那樣,馬歇爾開始討論時通常聲明“美國政府不容置疑的原則”,然后基于該原則分析具體的憲法表述,最后將這一分析適用于正在處理的案件。當然,在政治學看來,這并非是在中立地行使司法權力。馬歇爾對于他所提煉之原則帶有傾向性的闡釋體現了其解釋的才智以及技巧。盡管如此,這一方法將美國人和他們的過去聯系起來,也有助于實現其他的功能。該方法有時也影響了包括斯托里在內的其他大法官的意見。
馬歇爾法院發現自己卷入了關于如下問題的一系列爭論之中:州法院是否享有獨立的權力來解釋《憲法》。這些爭論為當代法律人所熟知。至于這些爭論是如何與有關州權的整個辯論融為一體的,他們則可能不那么熟悉。諸如麥迪遜和卡爾霍恩之類的人士認為,這些議題與更加引人注目的脫離聯邦問題、廢止聯邦法令問題存在密切的聯系。
弗吉尼亞最高法院在1814年亨特訴馬丁案中的判決是針對聯邦司法至上的最值得關注的挑戰。在同一訴訟的前一階段,合眾國最高法院已經撤銷了弗吉尼亞法院的裁判,并且判決:弗吉尼亞的特定法律沒收了費爾法克斯爵士的大量財產,違反了與英國的和平條約。最高法院撤銷了弗吉尼亞法院的判決并將案件發回重審,同時就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判決進行了簡單的指導。(今天,最高法院會更加委婉地將案件發回州法院,其理由將是:開始“與其意見不相抵觸的進一步訴訟程序”。)然而,在發回重審的程序中,弗吉尼亞法院判決:最高法院沒有權力審查其判決。這個州法院主張:該事項免受合眾國最高法院的上訴管轄,而規定最高法院具有上訴管轄權的《司法法》第25節是違憲的。因此,合眾國最高法院沒有權力向弗吉尼亞法院簽發糾錯令狀。
卡貝爾法官撰寫了弗吉尼亞法院的主要意見。他認為:雖然這兩類政府均受到《憲法》的約束,但它們是相互平行和獨立的。“因此,這兩類政府各自具有分裂之主權的一部分,盡管它們擁有相同的領土,管理相同的群體,時常也管理相同的事項,但是二者相互分離、彼此對立。”所以,“每一類政府都必須通過它自己的機關采取行動,除此之外,它不能在其權力范圍之內期望、控制或者強制民眾服從”。確實,州法院受到至上條款的約束。但是,這僅僅要求它們“遵循自己的判斷,履行自己的責任”,在其審理的案件中適用《憲法》。對于州法院,最高法院不享有上訴管轄權,否則就意味著,聯邦確實享有相對于分立之主權者的“優越地位”。
協同意見同樣耐人尋味。布魯克法官認為,《弗吉尼亞決議》為如下命題提供了依據:各州是“人民的以及各州自身權利的捍衛者”。他也強調,根據《邦聯條例》,邦聯國會必須依靠各州執行聯邦法律。而《憲法》的要義正是取消州政府的這種支配地位。“如果仍然依靠州的政府機關來行使其最基本的權力,共同政府的性質就會被完全改變,它將陷入一種低能的狀態,與前邦聯時期相差無幾。”畢竟,在《邦聯條例》之下,政府“巨大和根本的缺陷”就在于它依賴于各州的合作。羅恩法官也認為《弗吉尼亞決議》以及麥迪遜隨后撰寫的報告為上述命題提供了依據。他強調:《憲法》采用了新體制,基于此,“共同政府直接針對人民行使職權”,除了選舉總統和參議員的情況,無需各州政府的協助。的確.,如果州法官被視為聯邦司法機關的臂膀,那么他們就可能被強制審理如此之多的聯邦案件,結果,“他們事實上被迫離開了現職!”
弗吉尼亞的上述法官在1814年使用的某些措辭,會讓當代的憲法學者覺得熟悉。1992年,最高法院采用了類似的論點,以五比四的判決禁止國會要求州的立法者實施聯邦法律。多數大法官強調了從
《邦聯條例》之體制向《憲法》之體制的轉變,前者要求州政府的協助,后者則直接針對個人行使職權。但是,不同于1814年的弗吉尼亞法官,當問題涉及司法權力時,當代的最高法院一直不愿意遵循這一論點的邏輯。現在,該法院在強制州法院與強制州立法機關之間進行了區分。根據其意見,“在某種意義上,州法官確實被命令執行可由州法院執行的聯邦制定法,但是,這一類針對州法官的聯邦‘命令’得到了至上條款的文本授權”。因此,最高法院消除了先前羅恩法官的憂慮,即國會有可能強迫州的初審法院審理聯邦案件。上訴審查的議題現在得到了如此妥善的解決,后來的大法官因而不會再遇到如下困境:他們相對于州法院的權力可能被當作對州主權的侵犯。
今天,無人會質疑斯托里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為1816年馬丁訴亨特的租戶案撰寫的意見,其再次確認了該法院對于州法院的管轄權。在開始分析時,斯托里闡明了州政府與聯邦政府之間的關系。在
他看來,《憲法》“不是由各州通過其主權”制定的,“應當強調的是”,它是“由‘合眾國人民”’制定的。所以,聯邦權力并不是從既有的各州主權中分離出來的,二者均源自于人民。聯邦權力是在廣義上被界定的,原因在于:《憲法》的制定“并不僅僅是為了應對短短幾年的一時之需,而是旨在歷經滄桑歲月以及深鎖于上帝冥冥旨意之中的世事”。《憲法》第3條的文字規定了司法權力,表明了“全體美國人民鄭重聲明的立場,它建立了一個重要的政府部門,該政府在許多方面是全國性的,在所有方面是最高的”。《憲法》“并不僅僅針對個人”發揮效力,“也針對各州”發揮效力,導致它們“均”無法“實施某些主權性的權力”,同時在其他權力方面對它們進行限制。結束了國家主義的開場白之后,斯托里提出:制憲者已經預見到,屬于聯邦司法管轄權之內的案件也可能在州法院出現。如果“各州之主權的某些最高屬性被剝奪了……我們確實難以支持如下論點:針對州法院之判決的上訴審權力與我們制度的精神相背離”。既然聯邦法院
顯然有權力撤銷各州立法者和州長的違憲行為,為何卻不能撤銷州法院的違憲行為呢?
在馬丁訴亨特的租戶案審結的五年以后,最高法院遭遇了針對其上訴管轄權的另一次挑戰。柯恩斯訴弗吉尼亞案涉及弗吉尼亞一項禁制令的適用,該州禁止哥倫比亞特區的一種彩票在其境內銷售,被告將州的判決訴至最高法院。該州基于主權豁免予以抵制。簽發糾錯令狀將迫使提起該刑事訴訟的弗吉尼亞州到聯邦法院應訴。《憲法》第十一修正案禁止聯邦法院受理另一州公民針對任何一州的起訴,該州據此挑戰聯邦管轄權的行使。
雖然彩票法本身并不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弗吉尼亞人已經受到了聯邦法院的警告。(他們可能還關注國會管理哥倫比亞特區之廣泛權力的域外效力,該權力也曾被用于永久性地解放進入這一特區的所有奴隸。)聯邦法院似乎正在暗中擴張其權力。譬如,1820年,杰斐遜曾哀嘆道:“合眾國法院穩定的發展趨勢在于:突破各州權力與聯邦權力之間的憲法障礙。”1821年,他致信羅恩法官,后者是馬丁案中一個協同意見的作者,杰斐遜說:他最大的擔憂在于聯邦司法機關,該機關“如地心引力一般,悄無聲息地前行,不露聲色地推進,步步為營,固守所得”,從而“暗中”將各州并入聯邦政府。
馬歇爾主要基于其有關聯邦的總體構想,不同意州豁免的觀點。他說,“美國各州”“以及美國人民已經確信,一個緊密的和牢固的聯盟對他們的自由和幸福而言是必要的”。“除非各獨立州將其主權的很大一部分授予”這樣一個聯盟,該聯盟“將有名無實,從而使他們的所有希望落空”。若非最高法院對于州的刑事定罪加以審查,聯邦權力就可能被任何心存敵意的州政府所阻撓,原因在于:聯邦官員即使被宣判違反了違憲的州法律,也得不到聯邦的救助。的確如此,州法官總體上具有公信力,但是,州與聯邦政府之間的沖突會不時發生。對于《憲法》的解釋,既要考慮美好的時代又要考慮糟糕的時代。“《憲法》的制定是為了千秋萬代。”它將“經歷狂風暴雨”,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在組織上存在如此缺陷,以至于未規定確保自己的法律得以執行的手段”。馬歇爾說,各州政府沒有權利干涉憲法體制。人民制定了《憲法》也可以廢止《憲法》,“而這種制定或廢止《憲法》之不可抗拒的無上權力僅屬于人民整體;不屬于他們之中的任何一部分”。一部分人民干涉《聯邦憲法》的任何企圖“就是篡權,獲得人民授權的人士應當挫敗它”。
由于存在利益沖突,馬歇爾首席大法官不曾參與馬丁案的審判,他通過柯恩斯案獲得了處理聯邦最高法院與州法院之關系的機會。馬歇爾又一次采用了堅定的國家主義立場。“在諸多方面,而且是最重要的方面,合眾國已經成為單一的國家,這一點從不曾被否認。”在戰爭與和平時期,以及在“所有的貿易管理”當中,“我們是一個民族”。馬歇爾說,各州不是獨立的主權者,而是“合眾國的組成部分”——“一個龐大帝國的成員——從某些方面來看是主權者,從某些方面來看又是從屬者。”從邏輯上講,聯邦政府的司法機構在解釋聯邦法律方面應當是最高的。在這片國土之上,由每一個州的最高法院獨立進行解釋只能導致“矛盾和混亂”。此外,這種上訴管轄權的行使得到了《聯邦黨人文集》的容許,作為制憲的原始文獻,后者“一直被認為具有權威”。最后,馬歇爾評論道:當第一屆國會通過《司法法》時,它就支持關于《憲法》第3條的這種解釋,所有的州法院也都已經接受了該解釋,只有一個除外,后者的判決遭到了撤銷。
民主共和黨的報紙對這一判決感到震驚。《里士滿問詢報》擔心:“司法權力,邁著如時間那般無聲的步伐,帶著如死亡那般貪婪的個性,正在輕易地破壞州的權利。”但這一反應并非僅限于南方。一家俄亥俄的報紙宣稱:“最高法院以驚人的進度破壞《憲法》的聯邦主義原則,并基于此而建立強大的統一帝國,這有利于強大君主的王權得以形成。”羅恩法官試圖讓詹姆斯·麥迪遜抨擊最高法院的意見,但沒有成功。令羅恩失望的是,麥迪遜說:當與州法院的判決發生沖突時,聯邦法院的判決優先,這才是“更好的政策”。于是,羅恩自己承擔起了這一任務,將最高法院的裁判稱為“最荒謬的和最缺乏先例依據的判決”,該裁判只能說明:“所有的歷史告訴我們,對于權力的熱衷必定感染和腐化一切擁有權力的人。”杰斐遜也繼續對聯邦司法權表達不滿,稱它是“兼并的引擎”,主張國會采取行動來推翻柯恩斯案的判決。
在另外兩起重大的案件中,馬歇爾法院也限制了各州制衡聯邦政府的能力,含蓄地否定了州對聯邦法令提出異議的理念。奧斯本訴合眾國銀行案是圍繞聯邦銀行合憲性之長期斗爭的一個回合。合眾國銀行在俄亥俄遭到了激烈的反對,而最高法院先前確認該銀行合憲的判決在該州則受到了尖銳的批評。(一家報紙就這一問題發表了社論,題為:“合眾國銀行——無所不包!各州主權——一無所有!”)俄亥俄通過了一部法律,向合眾國銀行的每一個分支機構征收五萬美元的稅款。根據這部法律,州審計員拉爾夫·奧斯本決定扣留銀行的資金。該銀行取得了針對征收稅款的聯邦禁制令,但是州官員依然繼續執行州法律。在銀行拒絕繳納稅款之后,奧斯本的助手進入了銀行的保險庫,拿走了他們可以找到的所有東西,總價值達120 000美元。聯邦下級法院簽發法庭命令,要求其將資金歸還銀行。
如今,基本上只有聯邦法院管轄規則領域的專家熟悉奧斯本案,這主要還是因為最高法院在該案中的如下判決:聯邦法院可以審理合眾國銀行作為聯邦機構所提起的任何訴訟。不過,對于當下來說,聯邦法院針對州官員的禁制令則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基于州之主權豁免而阻止起訴的主張被馬歇爾所否定。州官員聲稱:在這起禁制令訴訟中,真正的被告應該是州本身,原因在于:該訴訟試圖“限制州的官員執行州法律”。馬歇爾承認:考慮到該州在本案中顯然具有直接的利益,他“感受到了這一論點充分的說服力,并且認可它提到的困難”。盡管如此,他依然毫不猶豫地駁回了這一論點。
馬歇爾強調了相反的裁決可能對聯邦至上所造成的影響。州官員可以“阻止合眾國境內任何法律的執行”。如果州行政官針對聯邦官員進行罰款或者處罰,后者將無法獲得禁制令。郵遞員、稅務員、聯邦法院事務官以及征兵人員都將面臨破壞性處罰的風險,例如,合眾國銀行就遭到了征稅。馬歇爾指出:總之,州將“能夠隨心所欲地攻擊聯邦,阻止它的每一步進展,積極有效地執行自己的規劃,而聯邦只能呆立一旁,被卸下了防御的盔甲”。
在第四個案件中,最高法院再次采取行動,以制止州干涉聯邦的活動。麥克朗訴西利曼案的原告主張:聯邦土地登記員未能應其要求進行登記,該行為違反了法律。他分別向兩個法院申請針對該登記員的職務執行令狀(職務執行令是強制政府官員履行其職務的法律令狀)。聯邦法院認為它沒有權力審查登記員的行為,以此為由拒絕受理這一訴訟。州法院則認為,它確實具備這種訴訟管轄權,但根據案情駁回了原告的主張。以上兩個裁判都被上訴至最高法院。約翰遜大法官的意見開篇便評論道:“州法院的標新立異使得法律權利糾纏不清,對于共同政府之權力的行使,它們也表現出越來越多的自負”,而這些案件就為此提供了“典型的范例”。約翰遜認為,聯邦下級法院拒絕受理聯邦的法律訴訟是正確的,他說:“基于什么法律依據,州法庭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行使向登記員簽發執行職務令的權力,要設想這一點并不容易。”約翰遜說,既然國會沒有將簽發執行職務令的權力留給聯邦法院,顯然可以推斷,國會也沒有將這一權力留給州法院。
綜合起來考慮,上述判決破壞了各州利用州主權來防御聯邦越權行為的工作。州法院不得就憲法議題進行獨立的裁判,它們從屬于聯邦最高法院。它們控制聯邦官員之行為的權力是有限的。如果州立法機關不同意最高法院的判決,認為聯邦制定法違憲,聯邦法院則可以制止其官員服從州法律,并且要求他們為損害承擔責任。這些判決體現了馬歇爾的觀念,它涉及聯邦司法機關在憲法體制中的作用。在一系列匿名的小冊子中,他更加具體地闡述了這一觀念,這些小冊子為最高法院而辯護,使其免受弗吉尼亞主要的州權主張者的攻訐。以“《憲法》之友”作為筆名,馬歇爾對于契約理論表示質疑,并且聲明存在一個整體意義上的美國人民。他問道:“我們的國家不存在嗎?”“前法國皇帝指責我們缺乏國家特征,或者并未作為一個國家真正存在過;但是,他并不否認我們在理論上和憲法上的存在。”“合眾國是一個國家;卻是一個由各州組成的國家,它們在許多方面,盡管并非所有方面,都是主權者。這些州的人民也是合眾國的人民。”簡而言之,“我們的《憲法》不是一份契約。它是單方的行為。它是合眾國人民的行為,他們在各自的州集會,為整個國家批準建立一個政府”。因此,“當適用于這類政府時.所有建立在結盟或契約理論上的論點都必定是站不住腳的”。馬歇爾駁斥了如下論點:作為全國政府的一部分,聯邦司法機關不能確定全國政府與各州之間所謂契約的含義。當然,“聯邦成員之間的每一個爭議都能得到和平的解決,整個聯邦要將這一點歸功于它的組成部分”。解決這類爭議是“政府的重要職責之一”,也是“其得以組建的重大目標之一”。這是對于聯邦至上強有力的肯定。盡管如此,馬歇爾的觀念并非沒有引起爭議。
摘自:《[精裝]林肯:在內戰中(1861-1865)(雅理譯叢)》,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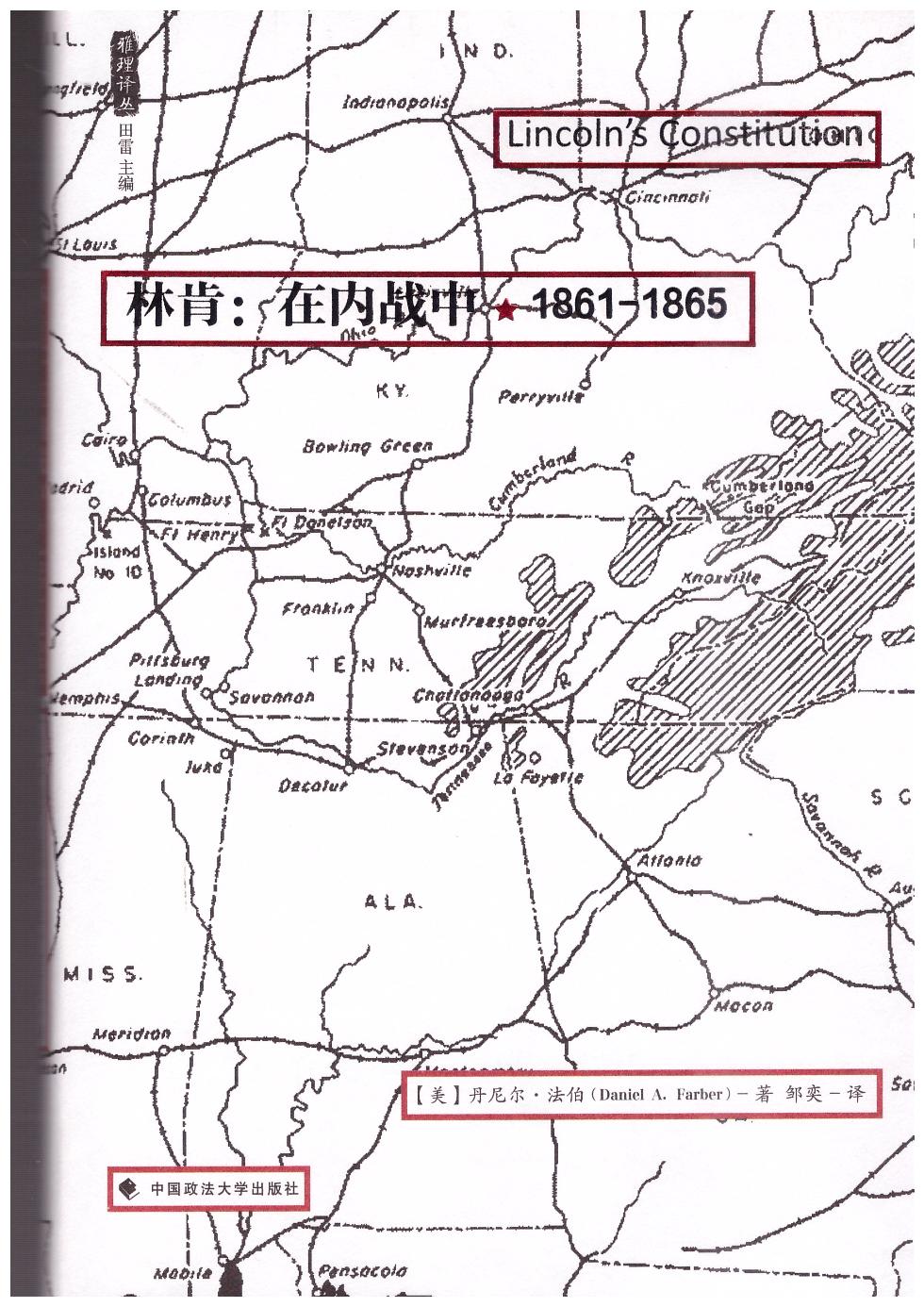 司法機關的回擊
司法機關的回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