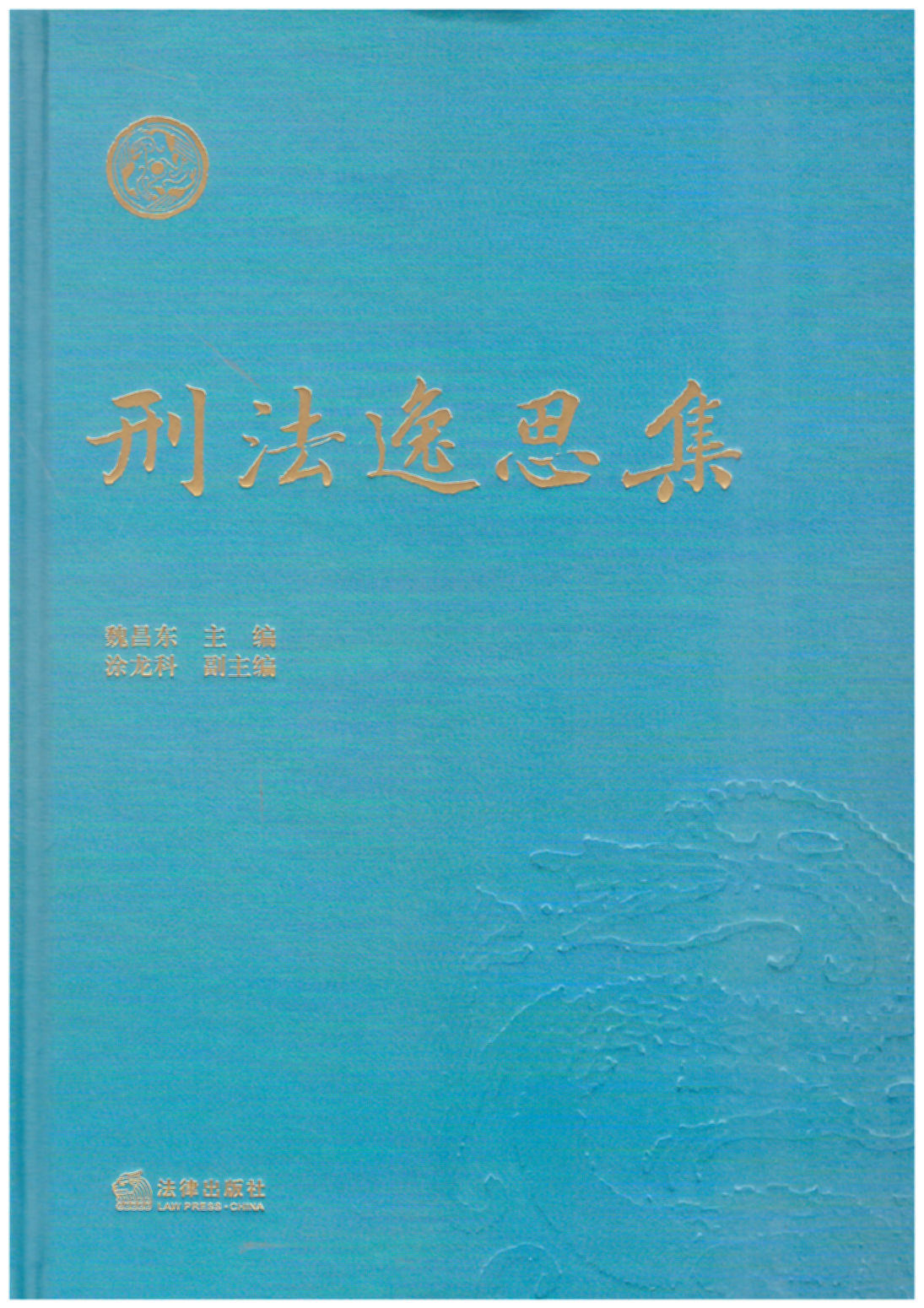
高利貸行為能否入罪
萬國海
【內容提要】高利貸行為在本質上是一種民間借貸行為,不屬于《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中的“非法發放貸款”,也不能被解釋為《刑法》第225條中的“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將高利貸行為認定為非法經營罪違反了形式判斷先于實質判斷的定罪規則,在定罪過程中,先進行實質判斷而入罪,有悖罪刑法定,破壞了法治原則。
【關鍵詞】高利貸 非法經營罪 刑法解釋法治
2009年1月22日江蘇省宜興市人民法院作出( 2008)宜刑初字第912號刑事判決書,認定被告人李某某、蔣某某(夫婦)向他人發放高利貸的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分別判處李、蔣二人有期徒刑四年和兩年半。根據江蘇省宜興市人民檢察院出具的宜檢刑訴( 2008)969號起訴書,基本案情是:李、蔣二人分別以其個人和宜興陶都寄售行名義向多個自然人高利放貸500多萬元,非法獲利112萬多元,其中以李、蔣個人名義放貸11筆,以李、蔣二人經營的宜興陶都寄售行的名義放貸1筆,共計放貸12筆。判決書認為:被告人李某某、蔣某某違反國家有關規定,擾亂金融市場秩序,情節嚴重,其行為均觸犯了《刑法》第225條第4項,應當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其刑事責任。一審判決下達后,兩被告人不服,上訴至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經書面審理后,裁定維持宜興市法院的判決,被告人又繼續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指定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理此案,2010年5月, 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再次審理了此案,最終認定被告人李某某、蔣某某二人構成非法經營罪,再次維持了宜興法院的一審判決。然而,筆者認為無錫、蘇州兩地法院對本案性質的認定值得推敲,在我國現有的法律框架下,發放高利貸的行為不應被認定為非法經營罪,其理由如下:
一、有悖刑法解釋的原理
從立法的沿革來看,非法經營罪是從1979年《刑法》中的投機倒把罪分解而來。取消投機倒把罪的原因在于該罪內涵龐雜、外延模糊,罪與非罪難以區分,故而在修訂1997年《刑法》時,取消了投機倒把罪,但為了彌補由此帶來的立法上的漏洞,又增設了非法經營罪。然而,97刑法頒布實施后很短時間內,為了打擊層出不窮的新類型的經濟犯罪,立法機關就不斷以單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形式對《刑法》第225條進行了補充和修改:1998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關于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第4條規定:“在國家規定的交易場所外非法買賣外匯,擾亂市場秩
序,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定罪處罰。”1999年12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刑法修正案(一)》中的第八條規定:“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增加一項,作為第三項:‘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非法經營證券、期貨或者保險業務的;,原第三項改為第四項。”2009年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刑法修正案(七)》第5條規定:“將刑法第225條第3項修改為:‘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非法經營證券、期貨、保險業務的,或者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的;”。可見,在十余年的時間內,人大常委會就以正式立法的形式對非法經營罪的進行了三次修改。除此之外,作為司法機關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又多次通過司法解釋,將若干種行為規定為非法經營罪。其中重要的司法解釋有:1998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騙購外匯、非法買賣外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1998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0年5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擾亂電信市場管理秩序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情節嚴重的傳銷或變相傳銷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2002年1月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非法經營國際或港澳臺地區電信業務行為法律適用問題的批復》、2002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生產、銷售、使用禁止在飼料和動物飲用水中使用的藥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2年9月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經營食鹽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3年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4年7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依法打擊淫穢色情網站專項行動有關工作的通知》、2005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9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0年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生產、銷售煙草專賣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這些司法解釋將非法買賣外匯,非法印刷出版物,非法經營食鹽,非法經營國際電信業務,在災害時期的哄抬物價、牟取暴利,擅自設立網上服務營業場所或擅自從事互聯網網上服務經營活動,非法傳銷,擅自發行、銷售彩票,在POS機上套現行為,非法經營煙草專賣品等行為都定性為非法經營罪。對于這種現象,學者龔培華指出:“非法經營罪的適用范圍的擴張越來越快,其與投機倒把罪的口徑越來越接近。非法經營罪正面臨著向投機倒把罪的回歸,罪刑法定原則正面臨著被突破的風險。”從實際情況來看,自從1997年《刑法》頒布實施以來,學界對非法經營罪的詬病就沒有中斷過,部分學者也曾極端地主張應當取消非法經營罪。然而,在我國經濟犯罪形勢十分嚴峻的情形下,非法經營罪的存在有其客觀必要性,貿然取消該罪是不現實的。筆者認為,在保留非法經營罪的情況下,通過合理的解釋來限制非法經營罪的范圍是較為可取的方法。
從規定非法經營罪的《刑法》第225條的法條來看,在解釋中最易產生爭議的是第4項“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如何合理地解釋這一行為類型呢?對這種概括性、開放性、極富彈性條款的解釋,最重要的是體系解釋。遵循同類規則是解釋刑法條文中“等”“其他”術語時必須堅持的體系解釋原則。正如解釋刑法第236條中的“其他方法”的含義,必須是與前面的“暴力”“脅迫”具有相同性質的,使被害人不能、不知、不敢反抗的方法。按照同類規則,根據《刑法》第225條前三項的規定,“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應當滿足以下三個條件:(1)該行為是一種經營行為,即一種以營利為目的的活動。(2)該經營行為屬于非法。從《刑法》第225條前三項的規定來看,非法經營行為均與國家經營許可制度有關。所以,這里“非法”的特定內涵是違反國家有關經營許可制度的法律、法規。國家關于經營許可制度的審定,往往與經營主體資格、經營條件和經營物品的范圍有關。(3)該非法經營行為嚴重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對照以上三個條件,本案中被告人發放高利貸行為沒有違反國家的經營許可制度,不屬于“非法”,且發放的筆數和金額有限,未達到嚴重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程度。因而,不能被解釋進非法經營罪。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前面提及的部分的司法解釋,嚴重違反了體系解釋的原則,將不屬于非法經營罪的行為類推為非法經營行為,如傳銷行為、哄抬物價行為、利用POS機套現行為等,這些行為并不必然違反國家有關經營許可制度,這部分司法解釋是不合理的,是值得反思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受不當司法解釋的影響,一些地方法院,將本不屬于非法經營罪的行為通過類推解釋或實質解釋作人罪處理。
二、有違定罪的思維規則
在刑事司法活動中,定罪是中心環節。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認定對被告人的權益影響巨大。嚴謹、細致、精確、全面是我們進行認定犯罪作業應當持有的審慎態度.而定罪的過程又是一個思維的過程,在這一思維的過程中,為保證定罪的準確性,我們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陳興良教授將這些規則概括為以下四點:客觀判斷先于主觀判斷、形式判斷先于實質判斷、類型判斷先于個別判斷、事實判斷先于價值判斷。這四個規則是建立在以德、日為代表的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基礎之上的,當我們遞進式進行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的犯罪認定作業時,就必然遵守這四個規則。首先是該當性判斷,而該當性判斷是形式的、類型的、客觀的、事實的判斷,然后才進入到第二階層的違法性判斷,在違法性判斷階段,是實質的、價值的、個別的判斷,而進入到第三階層的有責性判斷,才能進行主觀判斷。在層層判斷的過程中,每個階段都給行為的出罪留出了足夠的通道。因此,三階層的犯罪論體系,保證了定罪作業過程的科學性,將定罪過程以一定的程序固定下來,如剝繭抽絲,層層分解,符合定罪作業的嚴謹、細致、全面、精確的要求,大大降低了認定犯罪的錯誤率,也符合我們日常的思維習慣,因而是可取的和合理的。目前,我國刑法學界正在進行是否需要對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進行改造以及如何改造的激烈爭論。在此,筆者無意對三階層和四要件犯罪論體系的優劣進行評說,然而,從定罪作業的實用性上說,三階層犯罪論體系明顯優于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因為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所提倡的是平面的、對稱的、耦合的認定犯罪的四要件,這四要件在認定犯罪的過程中其作用是等量齊觀的,缺一不可的,所謂“一有俱有,一無俱無”,其前后的順序可以任意排列,隨意拼湊,一旦能湊足四要件就能人罪。四要件理論的最大缺陷在于其將認定犯罪這一嚴謹、復雜、精致的作業過程,演變為簡單的加減法,將認定犯罪的過程簡單化、表面化、形式化,難以應對復雜疑難案件。從多年來我國司法實踐的情況看,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造成人罪易而出罪難的現實問題,不能在犯罪構成內解決行為的出罪問題,難以兼顧刑法保護法益和保障人權的兩大功能,價值取向上偏向了犯罪打擊,保障人權的基本功能被弱化,難以真正貫徹罪刑法定原則。正是由于四要件的犯罪構成理論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也給我們的刑事司法實踐帶來了一些混亂。
三、與非刑事法律規定脫節
從犯罪的理論分類上來說,非法經營罪是典型的法定犯。法定犯的最主要特征是其“二次”違法性,即首先違反了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其次是違反了刑法的規范。從罪名上來分析,非法經營罪中的“非法”,是指構成該罪的行為首先違反了刑法以外其他非刑事法律。那么,高利貸行為是否“非法”呢?根據宜興市法院的判決,認定被告人高利貸行為違法的依據是1998年7月13日國務院頒布的《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第4條第3項的規定,即:“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擅自從事下列活動:……(三)非法發放貸款、辦理結算……”。對此,值得研究的問題是:以自然人和非金融機構的名義對外發放高利貸的行為是《辦法》中所規定的“非法發放貸款”的行為嗎?筆者認為不是。因為《辦法》中所規定的“非法發放貸款”,其前提條件是擅自設立金融機構,再以擅自設立的金融機構的名義對外發放貸款。如果不這樣理解,就只能得出任何自然人或單位對外的任何一筆收取利息的借款,都必須經過中國人民銀行的批準,否則即為“非法”的結論,顯然,這一結論是無法讓人接受的,也是不符合《辦法》的立法精神的。從經濟活動的現實看,自然人之間、單位之間或自然人與單位之間的有息借貸是經常發生的,這并不需要金融監管機構的批準,也不違法,即民間借貸并不為法律所禁止。《辦法》所禁止的是擅自設立金融機構而發放貸款的行為,相應地,《刑法》第174條所規定的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對此行為予以規制。本案中被告人以自然人和非金融機構的名義對外的高息借貸行為,在本質上仍然屬于民間借貸性質,不在《辦法》的禁止之列。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若干意見》的司法解釋,肯定了民間借貸的合法性,對于高息借貸的本金和四倍以內的同期利息法律是予以保護的。這也可以佐證:高利貸行為不是《辦法》中所規定的“非法發放貸款”。雖然《辦法》中有“設立非法金融機構或者從事非法金融業務活動,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提示性規定,但高利貸行為并不是《辦法》中的“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因而無法被認定為犯罪。退一步講,即使認為高利貸行為是“非法金融業務”,但如前所述,這一行為仍然無法被合理解釋為非法經營罪。在我國,由于附屬刑法規范不包括罪狀和法定刑,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刑法規范,即使存在“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而定罪處刑的依據仍然是刑法(包括刑法典、單行刑法、刑法修正案)。一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最終只能按照刑法的規定進行判斷。當然,對非法經營罪這樣的法定犯而言,如果判斷出該行為本身并不違法(非刑事法律),則可以徑直地得出不是犯罪的結論;而在行為違法的情況下,則需要根據刑法進行是否是犯罪的獨立判斷,這種判斷不能被非刑事法律中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條款所左右,“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條款僅僅是一種注意性規定,而不是判斷犯罪的依據。
四、背離法治的基本原則
法律必須被尊重,是法治的前提。在刑事司法活動中,法官認定行為性質的唯一依據只能而且必須是法律。在司法活動中,價值只能依附于規范而發揮作用。一定要堅守“規范先行,價值隨后”的原則,而不能倒置!規范的產生是一個價值遴選的過程,其中充滿了斗爭,當規范一旦形成,原先所有的價值都讓位于取得支配地位的價值標準,這一價值標準就是法律規范。對于認定犯罪來說,刑法規范是認定犯罪是首要標準,我們首先進行的是依據刑法規范的形式判斷,只有在形式判斷后得出肯定結論的情況下,才需要進一步進行實質判斷、價值判斷,而且,實質判斷、價值判斷的目的在于給行為出罪留足空間。也即只有在形式判斷入罪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實質判斷出罪。如果相反,首先進行實質判斷而入罪,再回頭尋找刑法中的規定,選擇一個與該行為最相類似的罪名而套用并予以定罪。這種定罪過程實質是類推定罪,完全違背了罪刑法定,徹底破壞了法治原則。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類似本案的情況時有發生。在司法過程中,面對具有一定社會危害性或利害交織的行為,我們的司法者往往本能地站在立法者的立場上,根據自身的價值觀念,首先對行為的性質進行實質判斷,在肯定行為具有社會危害的情況下.就會千方百計地將行為作入罪處理。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會在個別案件中實現個案公正,但其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法治的根基被動搖,法治追求的一般公正喪失。更為嚴重的是,導致認定犯罪沒有了規范標準,隨意出入罪,法律成了一紙空文。是否犯罪的認定則完全取決于司法者個人的內心信念或某種長官意志,這無異于重新回到了人治時代。當下,刑法學界內正在進行實質刑法觀與形式刑法觀之爭,筆者的基本看法是:實質刑法觀有利于消解法律穩定性與適應性之間的緊張關系,有利于個案正義的實現,有利于法律漏洞的修補,有利于解決司法實踐出現的疑難問題等。因而實質刑法觀具有一定的市場,尤其受到司法實踐部門的鐘愛。然而,實質刑法觀的最大危害是構成對法治極大威脅,動搖罪刑法定原則,甚至有導致法治倒退的潛在危險。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應有的警惕。形式刑法觀契合我國正在進行的法治實踐,總體來說,我國尚處于法治建設的初級階段,培養公民的法律意識,提高公民對法律的忠誠度和信仰度,是當前法治建設中的一個迫在眉睫的任務,要完成這一任務首先要求我們的司法者率先垂范,通過鮮活的司法活動,讓公眾切實感受到法律的權威和至上,培養公民對法律的忠誠和信仰,在刑事司法中,確保依法定罪處刑。因此,筆者認為,針對我國法治建設的現狀,在刑事司法領域,實質刑法觀應當緩行,現階段應當堅守形式刑法觀,待我國法治日臻成熟時,再提倡實質刑法觀,以彌補形式刑法觀之不足。
摘自:《[精裝]刑法逸思集》,法律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內容簡介:本書系顧肖榮研究員指導的碩士、博士以及學界朋友為慶賀顧肖榮研究員70大壽而編撰的學術文集,論文涵蓋刑法的基礎理論、法條解釋適用等方方面面,內容廣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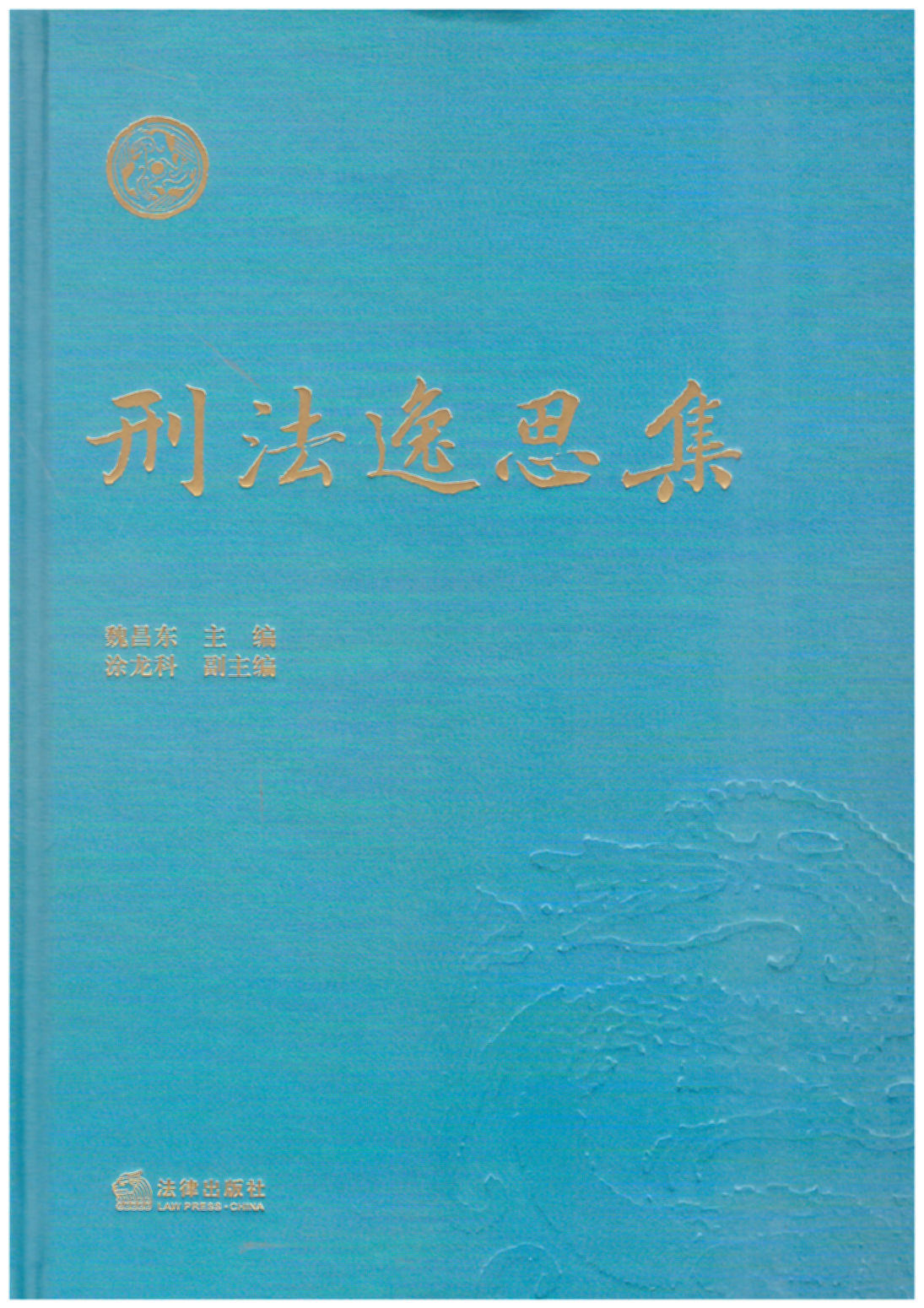 高利貸行為能否入罪
高利貸行為能否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