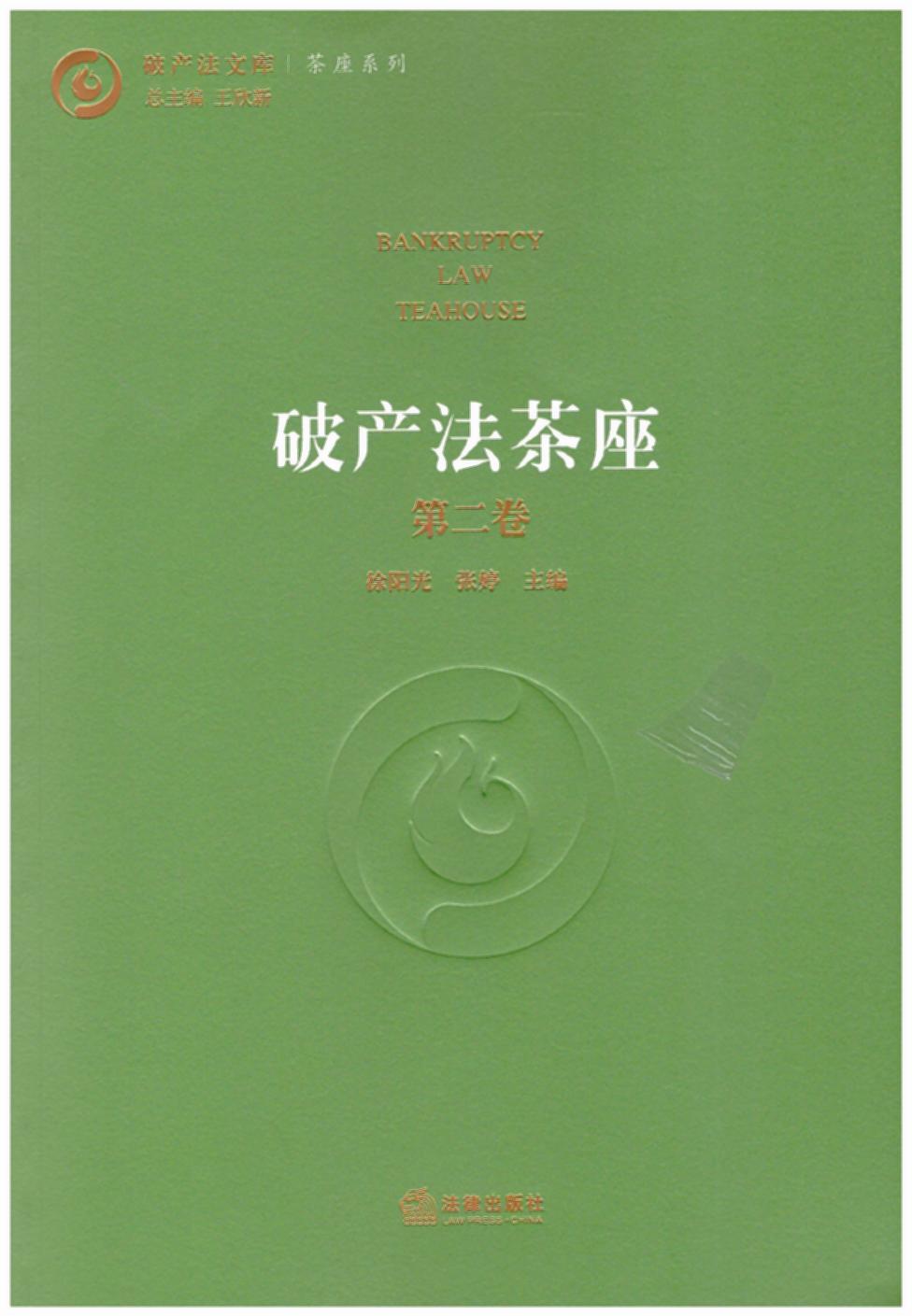
“三鹿”破產的法學困惑及大規模侵權破產的樣本意義
韓長印
三鹿集團破產案件已經過去很多年了,但筆者仍有揮之不去的法學困惑以及對于同類案件可能重演的顧慮。
據《廣州日報》2009年11月29日第A2版報道:“備受關注的三鹿奶粉賠償事件被畫上句號,結石患兒將無法從三鹿獲得任何賠償。”“記者昨天上午獲悉,石家莊中院日前作出裁定,終結已無財產可分配的三鹿破產程序。裁定中顯示,三鹿對普通債權的清償率為零。這意味著,結石患兒將無法從三鹿獲得任何賠償。”
一、隱含在“三鹿”破產中的法律困惑
(一)個別優先賠償的做法合乎情理卻不合法
據報道,三鹿集團等22家責任企業在“三鹿”破產之際先行向乳制品業協會支付9億元作為受害者的現金賠付,另撥出2億元設立賠償基金,這些做法雖然獲得了政府和社會公眾在心理上的普遍認可,但與《企業破產法》關于破產財產的處理方式和分配順序的規定是不相一致的。按照《企業破產法》第113條第1款的規定,破產財產清償順序是:“(一)破產人所欠職工的工資和醫療、傷殘補助、撫恤費用,所欠的應當劃人職工個人賬戶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費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支付給職工的補償金;(二)破產人欠繳的除前項規定以外的社會保險費用和破產人所欠稅款;(三)普通破產債權。”而因為產品質量問題造成的損害,受害人所應獲得的賠償,按照我國現行相關民商法的規定,應當一律列在上述清償順位中的第三順位。
(二)破產法關于董事、高管民事責任的規定形同虛設
《企業破產法》第125條第1款規定:“企業董事、監事或者高級管理人員違反忠實義務、勤勉義務,致使所在企業破產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對照該款規定,三鹿集團的董事、高管在明知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會對消費者的生命權、健康權造成危害的情況下,仍然指令公司繼續生產,其對受害人構成一般民商法上的侵權以及破產法上對債權人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的違反的事實至為明顯,但我們并未看到該案追究董事、高官民事責任的相關報道。這致使上述《企業破產法》的規定成為一紙空文。
(三)政府墊付費用的放棄追償可能助長大規模侵權行為的政府埋單
據報道,“三鹿牌嬰幼兒奶粉事件發生后,黨中央、國務院對此高度重視,在第一時間對嚴肅處理三鹿牌嬰幼兒奶粉事件做出一系列部署,立即啟動國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一級響應,對患病嬰幼兒實行免費救治,所需治療費用由同級財政預撥墊支,中央財政對確有困難的予以適當支持。這一系列措施對穩定社會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的確,以國家的公共財政對重大食品安全問題墊付相關救治費用本身無可厚非,這也是各級政府的職責所在。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如果這些費用墊付之后不向相關責任主體(該案中由于企業已經無產可破,應當指向相關直接責任人員)追償,不能最終轉由侵權企業及其直接責任人承擔,這不啻為“企業侵權行為風險的外部化”的負面案例,而企業違法行為風險承擔的外部化最終會助長侵權行為愈演愈烈。
二、“三鹿”受害人獲優先賠償的社會
認同及現行立法的邏輯矛盾
我們注意到,對于三鹿集團在瀕臨破產之前向中國乳制品業協會優先墊付醫療費用、死亡或者傷殘賠償款的做法,社會公眾在“三鹿”破產案件的處理過程中并沒有提出任何異議。可見,對生命權、健康權受到侵害的受害人的優先受償問題,社會公眾在倫理層面是普遍給予認同的。
實際上,《企業破產法》第113條第1款規定了兩個序列的一般優先權:(1)破產人所欠職工的工資和醫療、傷殘補助、撫恤費用,所欠的應當劃入職工個人賬戶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費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支付給職工的補償金;(2)破產人欠繳的除前項規定以外的社會保險費用和破產人所欠稅款。
從上述第一順位優先權的內容來看,其中“醫療、傷殘補助、撫恤費用”“應當劃入職工個人賬戶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費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支付給職工的補償金”,均屬于保障人身健康和獲得醫療條件的必需費用。這些費用的性質和用途絕大部分與生命、健康或者身體遭受“三聚氰胺”之害通常所計算賠償的項目、內容、性質和用途相吻合。從這個角度上講,無論這些費用是發生在破產企業的員工身上,還是發生在社會公眾身上,都應當予以優先賠償,如果這些費用不予賠償或者不能給予足額賠償,將直接影響受害人的生存和健康。
問題在于,《企業破產法》將破產企業所欠企業職工的上述債權列入優先權范疇,而對于企業之外作為社會一般人的人身損害賠償之債的上述費用和請求權列入普通債權,而按比例進行分配,其邏輯上的問題在于:同樣的債權性質、賠償責任類別和用途,僅僅因為債權人的身份不同,即一類系破產企業職工,另一類系破產企業職工以外的社會一般受害人,就“內外有別”地排列為高低不同的分配順位,這顯然有違設立這項優先權制度的初衷,未必能夠完全實現設立該項制度所追求的最終社會政策目標。畢竟,優先權在這個問題上的排序,不應當根據權利人的內外身份,而應當依照權利的性質(滿足基本生存需要和醫療等需要的最低社會保障性質)確定是否統一賦予其優先權順位。
三、“三鹿”作為大規模侵權破產的樣本意義
現代工業的發展,在環境污染、產品(食品、藥品)質量、安全生產等方面都催生了許多大規模侵權事件。該類事件往往因受害人數眾多、時間跨度較長、賠償金額巨大而極易導致侵權債務人破產。在侵權債務人破產之時,現行破產法所確立的擔保債權優先受償、侵權之債和普通合約債權平等受償的規則,往往使人身損害的受害人得不到必要的救濟,并且無益于實現侵權責任法遏制侵權行為之基本功能。
在我國,大規模侵權事件并不鮮見,甚至呈層出不窮之勢,比如安徽省阜陽市劣質奶粉致本地及其他地區嬰幼兒因營養嚴重缺乏而大量傷亡事件(又稱“大頭娃娃事件”)、中國東部濱海經濟帶由于環境污染而產生的“癌癥村”現象,以及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故導致的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為社會所廣泛關注的三鹿集團“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則屬更為典型的一例,只是說,“三鹿”破產把相關問題推到了社會焦點的浪尖之上。
更為嚴重的是,如果沒有物權法上的窮盡破產債務人所有可擔保財產的“浮動抵押”和“應收款質押”等制度存在,那么,企業破產時或許會給普通債權留下或多或少的責任財產(包括劃人職工個人賬戶之外的社會保險費用)而當物權法窮盡了擔保債務人可以用作擔保的一切財產,而不給普通債權預留哪怕是滿足侵權之債的受害人基本生活和醫療等費用的責任財產時,立法對普通債權,尤其是人身侵權之債的普通債權的“人道救濟”問題,就會凸顯。
本來,侵權行為法的立法目的有三:對受害人予以賠償、對侵權行為人予以懲罰、預防侵權行為的再次發生。但當實施侵權行為的企業陷入破產之時,侵權行為法的預防和懲罰功能基于侵權人的不復存在而失去原本的預防和懲罰意義,或者僅僅具有“畫餅充饑”的作用,對于受害人來講,補償的作用則可能凸顯為唯一可以期待的目的。
民商法理論研究表明,人身侵權之債除了侵權行為人的賠償之外,還有社會保障制度和商業保險制度等多元的救濟渠道,甚至未來侵權法發展以及與此相關的賠償補償體系的未來框架,主要應由侵權行為法、無過失補償制度、社會安全體系三者構成一個相對完善的補償體系,然后逐步從以侵權行為法 。擔負分配損害的主要機能的倒金字塔形轉向平方型(平衡型),即三方比重呈平衡狀態,最后漸次移向金字塔形。
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我國社會當下的社會保障水平只是處在一個“金字塔”的“塔尖”位置,其能夠發揮的救濟作用非常有限。故而,在社會救濟之外尋求不同利害關系人之間對風險的重新分配方案,仍然是我們萬般無奈而又必須作出的選擇。
在當下的破產實務和強制執行案件中,相關司法解釋已經注意并對該問題作出了不同的處置。《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二)》第16條規定,債務人對債權人進行的以下個別清償,管理人依據《企業破產法》第32條的規定請求撤銷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1)債務人為維系基本生產需要而支付水費、電費等的;(2)債務人支付勞動報酬、人身損害賠償金的;(3)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其他個別清償。又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第13條規定:“被執行人在執行中同時承擔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其財產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順序執行:(一)人身損害賠償中的醫療費用;(二)退賠被害人的損失;(三)其他民事債務;(四)罰金;(五)沒收財產。債權人對執行標的依法享有優先受償權,其主張優先受償人民法院應當在前款第(一)項規定的醫療費用受償后,予以支持。”但相關規定是否對所有的破產案件均具有普適意 義,仍有進一步思考的空間。
總之,如何重新審視并理順擔保物權、侵權之債、普通合約債權等不同性質的債權在破產清算程序中的地位及其應有的和諧關系,是大規模侵權致使侵權企業破產之時破產法所面臨的新課題。
摘自:《 破產法茶座(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微店鏈接: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2188426605
淘寶鏈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0760999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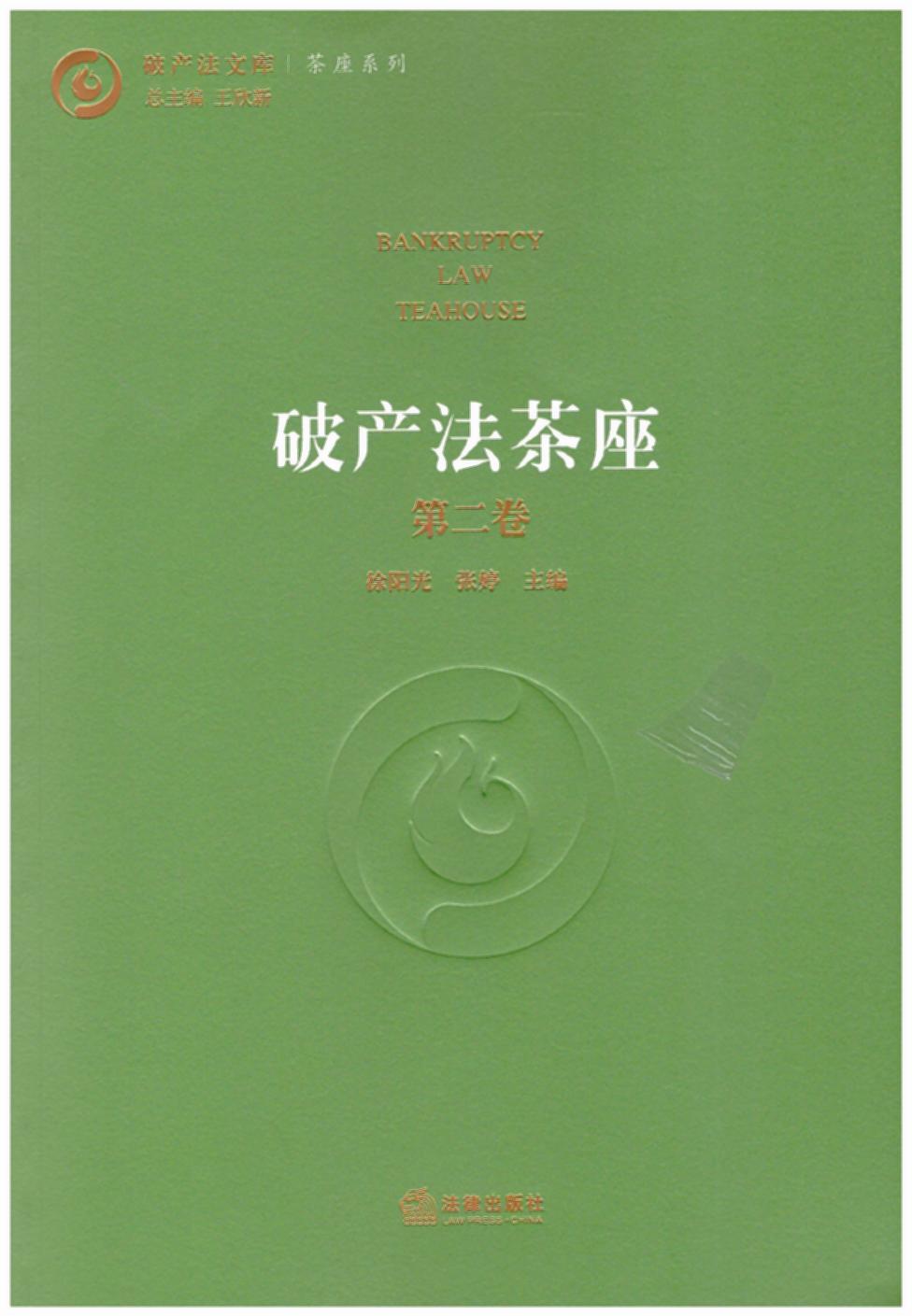 “三鹿”破產的法學困惑及大規模侵權破產的樣本意義
“三鹿”破產的法學困惑及大規模侵權破產的樣本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