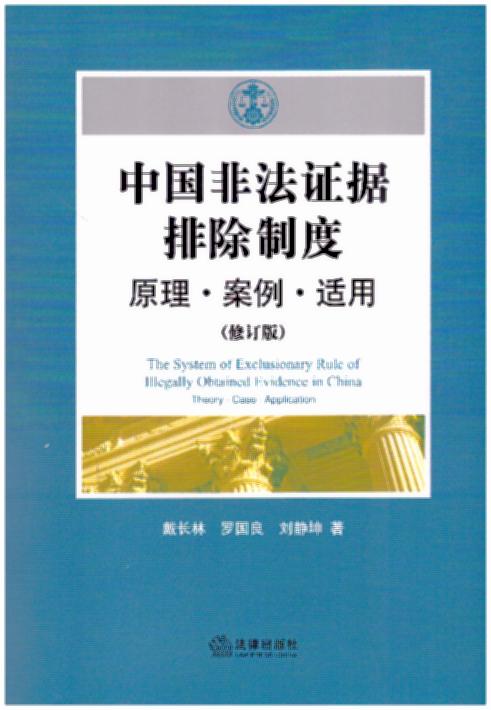
第二章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屬性與定位
在刑事訴訟制度發展史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一項比較新的制度。一般認為,該制度最初發端于美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為保障被告人的憲法權利,遏制警察非法取證行為,于19世紀末以判例形式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通過一系列判例逐步形成比較系統的排除規則體系。許多國家借鑒美國經驗,通過立法或者判例等方式確立了各具特色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產生相對較晚,對該規則的屬性和定位,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認識,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規則的實施效果。本章通過梳理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相關的理論和學說,明確該規則的基本屬性,并結合司法改革要求闡釋中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基本定位,以期澄清認識上的誤區,為進一步改革完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理清思路和方向。
一、非法證據的界定
中國傳統的刑事訴訟偏重實體真實,對程序公正的關注不夠。雖然在刑事訴訟法學領域,有關證據的“三性說”也包含證據的合法性,但這種合法性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也沒有相應的排除規則作為支撐。司法實踐中對證據的審查判斷,主要是圍繞證據的關聯性和客觀性進行的。
學術界從國外引進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相關理論后,一些人很自然地將非法證據和證據的合法性聯系起來。有學者認為,非法證據就是不具合法性的證據。也有學者將非法證據界定為不符合法定來源和形式的或者違反訴訟程序取得的證據資料,其外延不僅包括司法人員違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手段而獲得的證據,也包括證據的內容、證據的表現形式、收集證據的主體等因素不合法的證據。實際上,國外的非法證據是有特定含義的,并不等同于一般意義上不具有合法性的證據。準確地界定非法證據,不能簡單參照傳統的“證據三性說”理論體系,應當適用現代的證據能力理論體系。
(一)現代證據規則的主旨:證據能力規則
在刑事訴訟領域,自由心證制度取代法定證據制度后,有關證據證明力的審查判斷,屬于事實裁判者自由心證的范疇,法律不作預先規定。但并非所有證據材料都可以提交給事實裁判者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隨著訴訟程序的發展完善,基于各種技術和政策因素的考量,一些證據材料喪失了作為訴訟證據使用的資格。關于哪些材料能夠作為訴訟證據使用的證據規則,在英美法系通常稱為可采性規則,在大陸法系則一般稱為證據能力規則,為統一起見,本書采用證據能力規則的表述。
所謂證據能力,是指特定證據材料可以在訴訟中使用,據以證明案件事實的資格。這種資格并非是從事實層面上所講的哪些證據對案件事實有實質證明價值,而是源于法律的規定,是一種法律上的資格。由于證據能力規則直接決定特定的證據材料能否作為訴訟證據使用,因此,需要有明確的法律規則作為依據。這也是證據能力規則的特殊性所在。
隨著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分野,現代證據規則的重心轉移到了證據能力問題。誠如美國學者華爾茲所言,“證據規則決定一個事實認定者在解決事實問題時可以使用什么材料”或者說,“大多數證據規則都是關于哪些材料應當被采納為證據的問題。”顯然,對證據材料的證據能力所施加的規則限制使自由心證有了外在的法律邊界,這也使得刑事訴訟領域所認定的事實帶有了明顯的規則烙印。
廣義上的證據能力規則,既包括從正面規范證據收集、保管、固定、審查、運用等活動的指引性規則,也包括從反面否定某些證據材料作為訴訟證據使用的資格的排除性規則。從法庭審判的角度看,證據能力規則主要是指證據的排除規則。
證據能力理論的提出,對法庭審查判斷證據的模式產生了重大影響。由于證據能力的認定是審查判斷證明力的先決性問題,因此,法庭對證據的審查判斷要分兩步走:首先,要審查判斷特定證據材料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只有具備證據能力的證據材料,才有資格作為訴訟證據使用。對于沒有證據能力的證據材料,應當依法予以排除。其次,對經審查具有證據能力的訴訟證據,要結合案情和在案證據審查判斷其證明力,進而決定能否將之作為定案的根據。
證據能力規則的適用效果,與審判模式有很大的關聯。在普通法系法官——陪審團的二元式審判模式下,法官和陪審團分別負責裁決案件的法律和事實問題,為避免沒有證據能力的證據材料污染陪審團,如果控辯雙方對特定證據材料的證據能力存在爭議,法庭就應當在陪審團不在場的情況下對證據能力的爭議作出裁判。只有法庭認定具有證據能力的證據材料才能提交給陪審團,那些不具有證據能力的證據材料應當被排除在陪審團的視野之外。
這種制度框架下,證據能力與證明力的區分涇渭分明,陪審團不會接觸沒有證據能力的證據材料,證據能力規則的適用效果較好。相比之下.在大陸法系職權主義審判模式下,證據由職業法官進行審查判斷。對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審查判斷,是由同一名法官或者同一個合議庭負責進行,由于法官在審判前已經查閱案卷材料,通常了解“應當排除”的證據,即使法官認定特定證據材料不具有證據能力,因其已經接觸到該證據材料,再要求其完全排除該證據材料的影響是比較困難的。但是,由于非法證據不能作為判決的理由,因此,法院認定被告人有罪,必須在應當排除的證據之外,有充分的可采納的證據來支持有罪判決。換言之,法院在論證判決理由時不得引用被排除的非法證據,也就是不得將非法證據作為定案的根據。職權主義審判模式在運作過程中,實際上將證據能力由接受法庭調查的資格變成作為定案證據的資格,這種做法容易抵消證據能力規則的實施效果。德國學者魏根特就此指出,在德國的審判模式下,證據能力規則存在的意義只不過是為法庭論證判決增加困難而已。鑒此如何改革完善傳統的審判模式,使證據能力規則切實得以貫徹落實,是職權主義審判制度下需要認真研究的重大課題。
(二)非法證據不具有證據能力
中國傳統的證據法并未區分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兩個層面的問題,而是從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等方面對證據材料作出總體判斷,然后決定能否將該證據材料作為定案的根據。理論界最初討論非法證據,也是從定案根據的角度展開的,這實際上是將證據能力與證明力問題混同起來,或者將兩者捆綁在一起。沿著這種思路,如果非法證據經審查判斷是真實可靠的,具有證明力,似乎就不用排除了。這顯然不符合證據能力規則設置的初衷。
對于不具有證據能力的證據材料,根本就沒有作為訴訟證據使用的資格,也就談不上證明力的審查判斷問題。進一步講,證據能力是證明力的先決問題,不能跨越證據能力的審查而直接進行證明力的判斷。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的非法證據,就屬于不具有證據能力的證據,因其沒有作為訴訟證據使用的資格,故無須審查判斷其證明力。即使非法證據實際上是真實可靠的,但由于其不具有證據能力,因此不能作為訴訟證據使用,也不能無視其不具有證據能力的前提而將之作為定案的根據。
(三)非法證據是因取證程序違法并且侵權而喪失證據能力
中國傳統的證據三性理論,與現代的證據能力理論涉及不同的規則體系,不具有直接的對應關系。從證據能力的角度看,非法證據顯然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不合法的證據,后者的范圍要大得多。各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所指的非法證據均有特定的含義。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源地美國為例,在美國法律體系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非傳統的證據規則,而是憲法性規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為了維護公民的憲法權利而創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鑒于此,盡管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與傳聞證據規則、意見證據規則等均屬證據能力規則,但該規則的目的在于確保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落到實處。在美國法學教材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一般屬于憲法刑事訴訟領域的討論內容,不同于一般證據法領域的證據規則。在美國的語境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的“非法”并非違反一般意義上的制定法,而是指違反了憲法。在美國早期判例中,聯邦最高法院曾明確指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聯邦憲法第四修正案限制政府侵犯個人隱私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第四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實質內容。盡管聯邦最高法院近期趨于保守,認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僅僅是法院制定的規則,但仍主張該規則的目的是威懾違反聯邦憲法第四修正案的違法行為。
美國法院對非法證據的界定,著眼于遏制違反憲法取證的行為,關注的是憲法權利的救濟和保障。盡管美國學者通常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限定為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實物證據,并將該規則界定為“由法院所確立的在刑事審判過程中禁止采用違憲搜查或者扣押而或取得的材料的證據規則。證據排除規則是為了實現憲法第四修正案禁止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規定而設置的規則”,但實際上,由于美國的刑事訴訟法與憲法關聯緊密,刑事訴訟法保護的重要訴訟權利大多屬于憲法權利的范疇,因此,通過違反刑事訴訟法規定,侵犯刑事訴訟法保護的重要訴訟權利的方式取得的證據,都能夠被納入非法證據的范圍,非法證據已經不再僅指非法實物證據。1966年確立米蘭達規則后,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供述被納入非法證據的范圍。技術偵查、誘惑偵查等偵查手段出現后,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監控記錄等證據材料也被視為非法證據。可以預見,伴隨著偵查取證手段的不斷發展,偵查取證程序不斷規范,非法證據的范圍將會不斷擴大。
從各國的法律規定看,非法證據大致可以被分為以下兩類:
一類是采用酷刑等侵犯人身權和意志自由權的強迫方法取得的證據。例如,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采用虐待、疲勞訊問、傷害身體、服用藥物、折磨或者催眠等方法訊問,在刑事訴訟法準許的范圍外實施強制,以刑事訴訟法不準許的措施威脅,所取得的供述,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允許使用。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規定,采用壓迫方式獲取的供述應當排除,所謂壓迫”,主要包括“刑訊、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無論是否達到刑訊程度)”。澳大利亞1995年《證據法》規定,對當事人或者其他人采用暴力、壓迫、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方法取得的供述,應當予以排除。日本憲法和刑事訴訟法均規定,采用強制、拷問或者脅迫
的方法獲得的供述或者因長期不當羈押、拘留后獲得的供述,不能作為證據。
另一類是通過侵犯一般憲法權利或者重要訴訟權利的方式取得的證據。例如,英國《警察與刑事證據法》規定,如果警察訊問時違反了法律規定的獲得律師幫助、警告和告知、合適成年人在場、訊問筆錄、錄音等規定,法官綜合考慮案件所有情形包括獲取證據的情形,采納該證據將嚴重影響訴訟公平性的,對該證據應當排除。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權和獲得律師幫助權,但沒有規定訊問時違反上述規定的后果,不過,聯邦上訴法院在判例中確立了未告知沉默權取得供述的排除規則,除非有證據表明被告人已經被告知沉默權,或者被告人不反對其供述在審判時作為證據使用。日本判例法認為,當偵查程序構成重大違法時,為了抑制將來的違法偵查,應當排除非法證據。
從各國有關非法證據的界定看,大多強調違反法定程序和侵犯重要權利兩個要素。據此可以認為,非法證據,是指采用違反法定程序,并且侵犯憲法權利或者重要訴訟權利的方式取得的證據。根據該界定,并非所有違反法律規定收集的證據都是非法證據。一般意義上的不合法的證據也不是非法證據。法律之所以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就是因為取證違反法定程序并且侵犯憲法權利或者重要訴訟權利,基于程序公正和人權保障等訴訟價值考量,有必要否定非法證據的證據能力。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屬性
與早期的傳聞證據規則等傳統證據規則相比,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雖然同屬證據能力規則,但具有獨特的屬性,這使得其與傳統證據規則存在本質上的差異。
摘自:《中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原理·案例·適用(修訂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內容簡介:詳細闡述了改革歷程中面臨的問題和挑戰、相關問題的理論思索、制度設計的架構考量以及改革走向的遠景展望。同時,本書從全國各地法院選擇若干典型案例,就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的常見問題進行針對性的闡釋,可指導各級司法部門準確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2017年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本書根據該規定進行了系統的修訂。"
微店鏈接: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1908525400
淘寶鏈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58498344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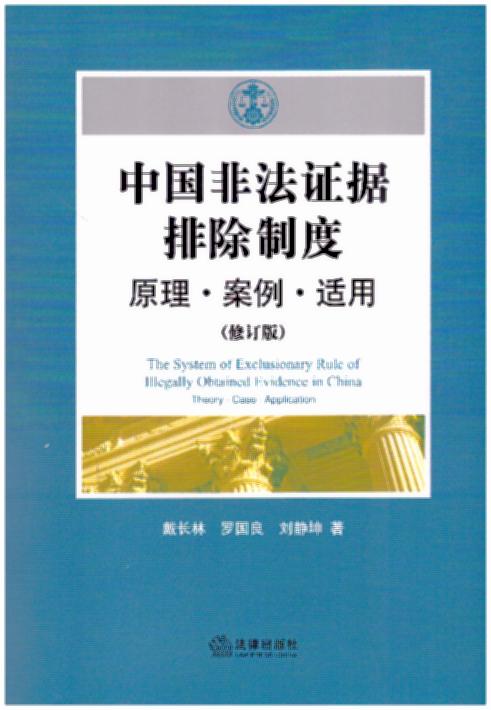 第二章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屬性與定位
第二章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屬性與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