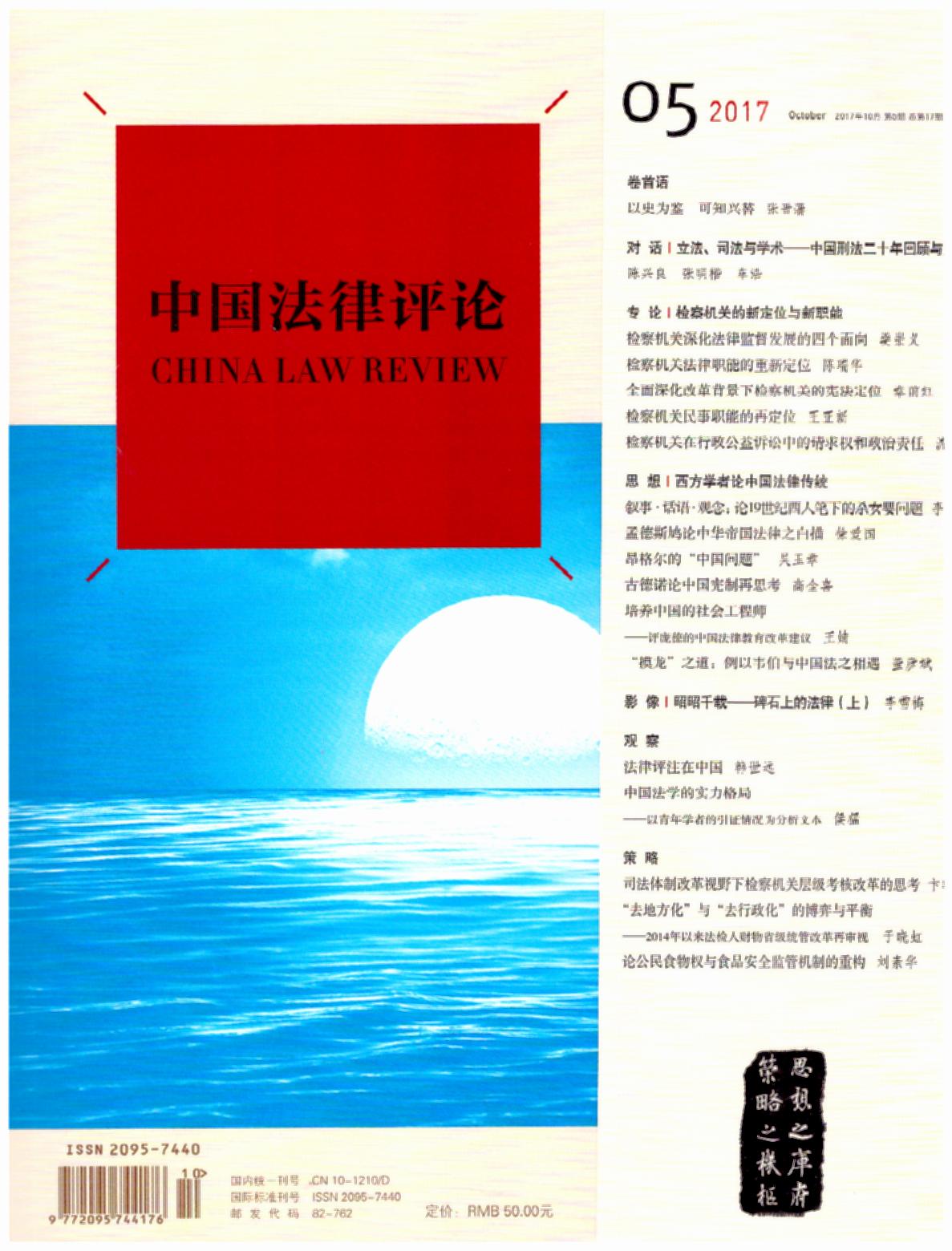
法律評注在中國
韓世遠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一、引言
隨著法學國際交流的頻繁,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其一,留學歐陸或者東洋的學人一定會對德國的施陶丁格民法典評注(StaudingerKommentar)、慕尼黑民法典評注(MuenchernerKommentar)或者“注釋民法”印象深刻、心儀不已;其二,歐陸或者東洋法律學人則會問起:在中國有與之相類似的法學文獻嗎?
確實,法律評注并非普遍存在的法學文獻類型。那么,這種特殊的法學文獻類型,其發生及發展需要具備什么樣的條件?它究竟具有什么魅力使得許多中國法學學人心向往之?在中國應否增添法律評注這種法學文獻類型?為此應做哪些準備工作?
要理解法律評注,不能不將它與一個國家的法、法源及法的運作過程聯系起來,與法的運作過程中的技術聯系起來。說到底,法律評注是一種工具,它的魅力恰來自它的工具理性。當下的中國盛行法律實證主義,成文立法成為主要的法源。立法者、裁判者各有其角色,與此同時,法律學人也有其無可替代的角色,法律評注作為法律學人的學術成果,可為法的運作過程帶來獨特的貢獻。本文通過分析民法領域的法學文獻,特別是其中的注釋書,描述其在中國的現狀,嘗試回答上述問題,并揭示未來發展的方向。
二、法的淵源與法學文獻
有什么樣的法,就會有什么樣的法學,以及與之相應的法學文獻。法律評注( Kommentar)作為一種獨特的法學文獻類型,其出現通常是以一部成文立法的存在為前提。
上述論斷很容易從大陸法系國家獲得驗證。德國的法律評注基本上是對《德國民法典》《德國商法典》等法典所作的評注。這種現象并不局限于國內法,也可以體現在國際法上。比如《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在德國便有相應的條文評注,而且還有相應的英文版本。
在像美國這樣的普通法國家,判例法( caselaw)為首要的法源,雖然法學著作要以某種形式將判例法規則體系化,使之易于成為學習的對象比如哈佛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蘭德(ChristopherColumbus Langdell)所編寫的合同法案例匯編書],使學生從中掌握法的原則,并使之能夠“像律師那樣思考”( thinking like alawyer),但這樣的著作與大陸法系的法律評注存在顯著的風格差異。
當然,在普通法國家也并非沒有像大陸法國家那樣的法律評注,比如,圍繞1872年《印度合同法》( the Indian Contract Act, Act 9 0f1872),從1921年起便有類似于大陸法國家的逐條法律評注書,而且已持續新版至2016年。顯然,這種著作并非針對判例法寫作,而是針對成文法,雖然在該評注書中結合了大量的判例。在美國,隨著《公約》的生效并成為其有效法源,也有美國學者寫作的《公約》逐條法律評注,并已成為該領域的經典。
中國向來是成文法國家,關于成文法的法學文獻,并不乏注釋書,也不乏注釋傳統。中國目前可知其具體內容的古代法律典籍,首推《唐律》。而關于《唐律》,早在公元649年中國便有了《唐律疏議》,它本身就是對于《唐律》律文提供的“定疏”。全書以律文為經,按照律十二篇的順序,對502條律文逐條逐句進行詮解和疏釋,并設置問答,辨異析疑。6由于官方組織編寫和推廣,《唐律疏議》在實踐中的結果遠遠超出了原來的編撰目的,已不僅是唐律的注釋書,甚至在唐代具有與律并行的實體法效力。從歷史上來看,中國人對于法律的評注恐怕要比西方人早。
清末變法,依舊以成文法為其主要淵源,在1911年完成了大清《民律(草案)》,主要借鑒《德國民法典》,采潘德克頓體例的五編制,總計1569條。然而,隨著清王朝在該年的終結,該民法典草案并沒有成為真正的法律。不過,對于該《民律(草案)》,中華書局1917年在上海出版了逐條的釋義書,作者邵義,是一位曾在日本留學的中國人。邵義還出版過一本關于1911年大清《刑事訴訟律》的注釋書。啟人思考的是,《民律釋義》并非“以解釋現行法為中心”。與其說它是以實務為導向,毋寧說它是以傳播新學新知為目的,是在借《民律(草案)》之體而傳播西方民法的新知識、新觀念。
在1929年中華民國《民法》頒布后,也曾相應出現了一批注釋書。比如史尚寬著《民法總則釋義》(會文堂新記書局1936年),歐陽溪著《民法總則釋義》(上海法學編譯社1940年),張正學、曹杰著《民法總則注釋》(商務印書館1947年)等。該部法典自1949年在中國大陸被廢除,但如今它在我國臺灣地區仍然有效。雖然有成文法典的條件,但在我國臺灣地區尚未產生大型的法律評注,對此后文仍將述及。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民法的發展在前30年(1949年至1978年)基本上停滯不前。在這30年中,1950年的《婚姻法》是唯一一部真正生效的民事法律,直到1980年被新的《婚姻法》所取代。盡管有兩次起草民法典的努力,但均因政治運動而中斷。而“文化大革命”期間,公檢法一度被砸爛,更談不上起草民法典。自1980年往后,中國的法制開始步入正軌。成文立法成為最為重要的法律淵源,同時,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也是法律淵源的組成部分。2010年,作為司法改革的重要舉措,最高人民法院推行中國特色案例指導制度。該制度意在學習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但到目前為止,尚沒有見到明確的規定要求法官必須遵循指導性案例。指導性案例的功能及效果,尚有待實踐檢驗。與之相應的法學文獻,將在下一部分分析。
三、當代中文法學文獻
(一)總體描述
當代中文法學文獻主要由期刊學術論文、學位論文和圖書組成。期刊學術論文和學位論文可以很容易地從“中國知網”數據庫找到,此處筆者僅就圖書進行描述和分析。當代中文法律圖書主要包含教科書、注釋書、專著(專題著作)和翻譯書。就教科書而言,如今法律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在中國的法學院使用率最高。這兩家出版社各有法學教科書系列,每個系列均不下40種。另外,北京大學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以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等,也出版了許多高品質的法學教科書。每年出版的法學專著,盡管沒有具體的統計數字,但也相當可觀。法學翻譯書深受法學學者和學生的歡迎,粗略估計,其規模也己累計達數百甚至上千種。這類著作的原始語言以英語、德國和日語居多。本文的關注點在于注釋類圖書。
1.1949-1979年
在這一階段并沒有出現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注釋書,其原因值得探討。在這一階段以民法為寫作對象的書籍,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基本問題》為代表。將該書作為范例,或可給我們一些啟發。基本的問題是:該書應該如何定性和歸類?
(1)解釋論vs立法論
該書是為了適應在職政法干部學習參考的需要而編寫,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總體上應屬解釋論。它力求描述新中國成立8年后的中國民法,編織中國民法學的知識體系。關于法及法源,認為“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示;而法規,則是其表現形式,是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法律、法令、決議、命令等法律文件”(第10頁)。中央一 級頒布的民事法規或其內容與民法有關的法規,共有747件(第11頁)。“我們國家制定民事法規,首先是把勞動人民的意志集中表現為黨的政策,經過實踐的檢驗,然后總結上升為法律。”(第11頁)客觀地說,這時期“政策”已是實際上的法源。
(2)階級性vs繼承性
這個時期特別強調法的階級性, “民法,是階級斗爭和階級矛盾的產物,它是統治階級在根本財產利益的問題上進行階級斗爭的工具”(第4頁)。廢除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解放前農民及其他勞動人民所欠地主的債務一律廢除,均是具體表現。
該書中大量使用的法律行為、代理、時效、所有權、債、合同、侵權行為等概念及制度,顯然又不是憑空的創造,這類學理的體系構造是借鑒蘇俄民法的結果,典型的特征是,將婚姻家庭法排除在民法體系之外。而蘇俄民法又具有繼受羅馬法、法國法乃至德國法的基因。因而,繼承性、共通性的因素,顯而易見。
(3)何以沒有法律評注作品
如果將法律評注理解為對于某部成文立法的逐條評注,在這個階段,除了一部《婚姻法》,其他的民法分支,并無正式的成文立法,況且按照當時的觀念,《婚姻法》尚不屬于民法。可見,當時并不具備出現逐條評注形態的法學作品的前提。
2.1980年以來的民法注釋書
新中國主要的民事法律都是在1980年以后陸續頒布的,構成了注釋書寫作的前提條件。
在1986年《民法通則》頒布后,便出版過注釋書。該書是逐條注釋,由兩位參加過民法通則起草工作的人士寫作完成。1995年6月30日頒布《擔保法》,此后也出版過一本關于該法的逐條注釋書,該書也是由立法機關人士寫作。
后來,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釋義叢書”,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到目前為止,在民事法律領域該叢書出版了合同法、婚姻法、合伙企業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民法總則等。就該系列釋義書的特點,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外國私法與比較私法研究所樸法眼(D r.K.Pissler)研究員曾指出:
(1)該系列的釋義書是由高級別官員( high-ranking 'cadres)擔任主編(比如在合同法卷釋義書出版時,主編胡康生先生任全國人大法工委主任;又如民法總則卷出版時,主編李適時先生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黨組成員,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
(2)各條文注釋的寫作者并不注明(比如,2017年出版的民法總則的釋義書,僅在“后記”中提及參加該書撰寫工作的作者,讀者無法確知具體條文釋義的作者);
(3)通常是在所釋義的法律頒布后很短的時間內便出版(令人猜想作者掌握有關立法者意圖的內部知識)。除了上述特點外,我們還可以繼續指出:
(4)該系列并不使用腳注或者尾注,讀者難以判斷相應觀點是屬于作者原創抑或有所出處。
(5)極少關注或反映司法實務(主要是司法判決)。
另外一套注釋書系列是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編寫。與前一系列相比,這一系列依條文具體區分“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以該系列中的物權法卷為例,其中的“相關規定”不僅包括中國的法律、行政法規及司法解釋的規定,還包括可進行比較的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的立法規定。這可以說是一項重要進步。不過,在不使用腳注或者尾注這一點上,該系列與前一系列相同。
除了法律之外,司法解釋屬于另外一類注釋書的評注對象。就此,首先須提及的是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叢書系列”。在
該系列叢書中,人們可以發現對于大多數重要司法解釋的注釋,包括關于民事案件訴訟時效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關于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的理解與適用、關于審理城鎮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案件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關于審理旅游糾紛案件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關于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關于融資適用合同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關于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關于物權法司法解釋(一)的理解與適用等。以關于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為例,該注釋書的主編奚曉明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后因涉貪腐問題入獄),作者絕大多數為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個別高校法學教授。該書不僅列明了撰寫人的姓名,而且在“后記”中按撰寫順序清楚交代了每位撰寫人的寫作分工。該書針對每個條文,依“主旨”“釋義”和“適用”的結構順序,逐一注釋。該書不僅使用了腳注注釋,而且還使用了案例以說明重要的問題點。
以上所描述的基本上是權威機構就法律或者司法解釋寫作的注釋書,除此之外,在中國也有學者參與寫作法律注釋書。比如,在合同法出臺之后,中國政法大學江平教授主編出版了合同法的注釋書,該書的特點是:多位作者的合著作品、沒有標注各位作者具體寫作的部分以及沒有使用腳注。在物權法出臺之后,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孫憲忠研究員主編出版了物權法的注釋書。較之江平教授主編的合同法注釋書,該書在兩個方面有所進步:標注清楚每位作者具體寫作的部分,并且使用了腳注。另外還有朱巖等學者的物權法注釋書。在民法總則頒布后,中國人民大學王利明教授主編出版了相應的注釋書。以上舉例,均屬合著作品。有時,我們也可以見到單個作者獨立寫作的注釋書,比如中國政法大學王衛國教授曾就破產法出版過獨著的注釋書,這是一本針對破產法的逐條注釋書,使
用了腳注注明引用,除了“注釋”,該書還使用“示例”就重要問題作進一步的說明。
注釋書的寫作不僅以國內的法律和司法解釋為對象,也有以國際條約為對象的。比如,針對《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已出版有張玉卿先生的注釋書和中國政法大學李巍教授的注釋書。
(二)整體分析
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輯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釋義叢書”而言,一如在其“出版前言”中所言, “該叢書堅持以準確地反映立法宗旨和法律條款內容為最基本要求,在每部法律釋義中努力做到觀點的權威性和內容解釋的準確性”。不過,這套釋義書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該系列釋義書的基本定位為宣傳法律的通俗讀物。比如在民法總則釋義書“后記”中所言,是“為了更好地宣傳民法總則,使社會各界對民法總則內容有全面、準確的了解,保證民法總則的順利實施”而編寫,
“力求簡明扼要、通俗易懂,便于準確把握立法原意”。由于其定位的目標讀者是“社會各界”普羅大眾,故而該系列釋義書的學術色彩不濃。比如,完全不使用腳注。其次,該系列釋義書各冊約有十至二十位作者,不同作者寫作風格存在差異,不易統一。以其中的合同法釋義書為例,第二章“合同的訂立”有63頁;而第七章“違約責任”盡管在實務中非常重要,在該書中卻僅有14頁的篇幅。
反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叢書”,由于其定位的目標讀者是法官、律師及學者,則顯得更為專業一些。該系列注釋書的編寫也“努力采取學說論證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不過,該系列注釋書也有其局限性。由于其作業絕大多數是法官,他們往往難以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花在注釋書的寫作上,而這類注釋書往往又是與相應的司法解釋的發布同時出版,或者緊隨其后出版。
就學者所寫的注釋書來看,仍有較大可提升的空間。首先,與由官員或者法官寫作的注釋書相比,由學者寫作的注釋書數量偏少。這恐怕與釋義書使注釋書“污名化”脫不了干系,好些學者因此而不太看重單純的逐條釋義,現有學術評價體系也不太把這類書當回事。其次,學者寫作的注釋書,無論是在學術圈還是在實務圈,大多尚未產生重大的影響,這也可以說是前一問題帶來的直接后果,投入不夠,自然回報不豐。
意識到中國現有的法律注釋書的不足,越來
越多人開始期盼理想的法律注釋書。
四、法律評注魅力何在
(一)法律評注是立法、司法及學說成熟的標志
理想的法律評注是什么樣子的呢?典型的例子可以舉德國的民法評注,大型的如施陶丁格民法典評注或者慕尼黑民法典評注,中型的如帕朗特民法典評注(Palandt BGB)或者埃爾曼民法典評注(Erman BGB),小型的如堯爾尼希民法典評注(Jauemig BGB Kommentar)或者民法典評注手冊(Handkommentar BGB)。如以日本的民法評注為例,其中大型的當然是有斐閣出版的“新版注釋民法”;簡明版的有日本評論社出版的“基本法注釋”(基本法)系列,民法系列具體包括民法總則、物權、債權總論、債權各論1(契約)、債權各論2(事務管理、不當得利、不法行為、制造物責任法)、親族、相續各冊,最初面世于1971年,后面不斷修訂。較之大型注釋書,簡明版注釋書修訂更新快,價格親民,更易為學生使用。另外,也有便攜版,比如松岡久和與中田邦博兩教授主編的《新民法評注(財產法)》(日本評論社2012年版)。民法評注的范例還可以從瑞士、奧地利、韓國等國家發現。通過這些事例,人們所能看到的不僅僅是“紙面上的法”,也能夠看到“訴訟中的法”或者“活法”。如此,法源便由實定的法律擴展至裁判案例(判例),甚至學說理論(學理)。
理想的法律評注并不容易完成。臺灣大學王澤鑒教授曾就日本注釋民法的編寫及出版寫道:
最近日本集合學界及實務界之力量完成注釋民法(全二六卷),由中川善之助、柚木馨、谷口知平、於保不二雄主編,有斐閣出版。日本學者頗為自豪,實有理由,蓋非累積數十年學說及判例之研究,不克完成此類劃時代之巨著也。
王澤鑒先生“希望能在十年內集合眾力,完成一套類如德國施陶丁格民法典評注、慕尼黑民法典評注,或日本‘注釋民法’之中國民法注釋書”。王澤鑒先生言此宏愿是在一篇名為“民法五十年”的報告中,推算時間應該是在1979年。時至今日,38年己過,在臺灣地區尚未出版上述大型的民法注釋書。又依王澤鑒先生在1995年的記述,以臺灣民法注釋的基本條件業已初備,“行政院”科學委員會特自1994年起,專案補助臺灣大學法律學系負責籌劃從事民法注釋工作,預計二年內先完成民法總則。顯然亦未克成事,足見寫作和出版大型民法注釋書,何其艱難。有學者稱法律評注為“法教義學的巔峰”,自然有其道理。
著眼于中國大陸,經過近三四十年的法律發展,已經有了相當的裁判案型及學說理論的積累,是在中國改進法律注釋文獻的時候了。
(二)法律評注是法律適用的有用工具
由于法律的專業化和精細化,每個法官、仲裁員或者律師只能是某一具體法律領域的專家。而法律的適用卻是綜合的,這意味著他思考法律問題時需要兼顧實體法與程序法,有時需要兼顧私法與公法。于此場合,一部詳盡的注釋書對于法律適用者無疑會有巨大的幫助,因為它對于某一具體法律條文提供了集中和詳盡的信息。
(三)法律評注有助于法律學習
對于法科學生而言,法學教科書自屬必要,但僅有教科書尚有不足。教科書傳遞給學生的只是法學的基本知識,許多學生可能希望更進一步探究。如此,如果有權威的專家學者撰寫的注釋書,能夠告訴讀者主流法官的立場以及學界的觀點,無疑會是非常大的幫助。
(四)法律評注是法學研究的重要一環
可從兩個層面說明。首先,一套法律評注的權威性往往與其作者或者作者群體有著直接的關系。以日本的“注釋民法”為例,不僅其編集代表均是日本民法學界的領軍人物,而且就具體條文的寫作者的挑選,也有其嚴格的學術標準,往往是在日本就該具體問題有專門研究的、學術圈公認的頂尖學者。比如,《日本民法典》第415條(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和第416條(損害賠償的范圍)便是委托北川善太郎教授執筆,新版則由潮見佳男教授修訂;第420條和第421條(賠償額的預定)則委托能見善久教授執筆;第423條(債權人代位權)、第424條(詐害行為撤銷權)等則委托下森定教授執筆。同時,正是因為有這樣嚴格的學術標準,能夠入選作者團隊,本身便是非常高的學術榮譽,又會因此激勵著作
者認真寫作。
其次,中國的許多民事法律是比較法的產物,具有混合繼受的特點,學習對象兼及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合同法》便是一個典型事例,立法者的任務固已完成,留給司法者及學者的任務卻異常繁重。法律評注的寫作本身便是解釋論的展開,而解釋論的展開必然是以“整合解釋”為歸趨:這也就意味著“法典繼受”后,我們無法通過簡單的“學說繼受”來代替中國學者對于《合同法》的解釋論作業,我們無法通過翻譯外國的教科書來代替中國的教科書。中國法官及學者,任重而道遠。
不妨舉一事例,說明何以學者對于法條的解釋不能僅限于字面的含義,而須從體系的視角作整合的解釋。《合同法》既繼受了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權(Unsicherheitseinrede,第68條和第69
條),又繼受了普通法系的先期違約( anticipatorybreach,第94條第2項和第108條)。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對方當事人解除合同,是否要以“催告”為要件?僅看第94條第2項字面表述,沒有提及“催告”,故按字面解釋當然不需要。可是,如果按照體系解釋,則會得出不同的認識。因為不可否認,《合同法》第69條規定的情形與第94條第2項中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的情形,會存在重合的現象。而按照第69條的規定,實質上對解除權的發生要求了“催告”。故對于這兩個條文,宜采體系解釋的方法,對于第94條第2項中“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的情形,進一步要求解除權的發生以“催告”為前提。由此可見,解釋論的展開有時難以通過單純地繼受大陸法系或者普通法系學說來完成,從體系的視角作整合解釋,這樣的工作只能依靠了解和關心中國本土實踐及理論的學者。
五、以民法評注作為學者對于法的運作過程的貢獻
徒法不能自行,法的運作過程必然要依靠人。立法者對于法的運作過程的參與是借助于制定法律;最高人民法院通過發布司法解釋也分享了這一角色。那么,法律學者借助于什么參與法的運作過程呢?學者的主要貢獻在于其學說理論,對于法的運作過程的參與也主要是借助于其學說理論。法律或者司法解釋的權威性屬于“權威的力量”(ratione imperii),而學者學說理論的力量則來自于“理性的權威”(imperio rationis)。
(一)法學理論:立法論抑或解釋論
民法理論大抵可以分為兩類:立法論與解釋論。前者關注如何設計出合理的民法規則或者規范,或者如何改進既有民法規則或者規范。這類理論的目標是要給民法立法者以指引,對之產生影響。后者則是遵循一套解釋方法(法學方法)以解釋既存的民事法律,幫助法官正確地適用法律。如果說前一種理論屬于一次性使用的理論,后一種理論則是可以反復使用的理論。隨著中國民事立法日趨完善,對于立法論的需求漸趨萎縮,而對于解釋論的需求則變得越發突出。因而可說,作為解釋論的法律注釋作品,屬于一個成熟社會所持續需要的事物。
如今,民法注釋的時代已經到來。
(二)民法注釋書的前提條件
日本的大型民法注釋書是26卷的“注釋民法”,最初面世于1964年,陸續刊行。及至1988年,更行刊出“新版注釋民法”,規模增至28卷。人事雖有更替,注釋民法的修訂不輟。在“注釋民法”刊行詞中,作為“注釋民法”編集代表的中川善之助、柚木馨、谷口知平、於保不二雄、川島武宜和加藤一郎共同寫道:
大型注釋書的刊行要以判例、實例以及學說等的充分蓄積為前提。我國向來欠缺大型注釋書,人們可以說這是由于日本法學的抽象化、概念化的性格所致,同時人們也無法否認,對于現代私法的體驗的缺乏是其主要原因。如今我們策劃刊行“注釋民法”,這正是由于我們認為,鑒于法體驗的蓄積以及民法學的發展,刊行大型注釋書的時機已經成熟。
與之相似,在臺灣,王澤鑒教授也曾指出:
注釋書的主要特色在于對某個法律的條文說明其規范目的,闡明條文間的體系關聯,綜合整理學說與判例,分析討論解釋適用的問題。注釋書的出現,須要具備若干條件,特別是要有系統的判例判決匯編及豐富的學說見解。
(三)理想的民法注釋書應是什么樣
就理想的民法注釋書而言,應能匯集判例及學說,自屬當然。這使人不禁想起比較法大師恩斯特,拉貝爾(E.Rabel)曾經說過的話: “有法律而無相關判決,猶如僅有骨骼而無肌肉。通說理論系法律之神經。” -部理想的民法注釋書, 應能將法律規范與裁判見解以及學者通說集合成為一個有機體。換言之,法律評注所描述的,雖是以成文法條為對象,卻要更進一步,描述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有機的并不斷成長的法秩序。
首先,民法注釋書是以實證法為中心。如今,中國主要的民事法律包括民法總則、物權法、合同法、侵權責任法、婚姻法以及繼承法等。注釋書不僅要說明法系條文的規范目的,也要提示不同條文之間的體系關聯。
其次,民法注釋書應當將法官對于法律發展所作的貢獻整合進法的體系。此所謂法官的貢獻不僅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也包括裁判案例及其呈現的具體裁判規范。筆者倡導發現具體的裁判規范:
重點是指發現那些對于現行法規范體系構成實質性發展或者增長的具體裁判規范(比如“權利失效”規則已出現在我國的案例中),這里看重的是規范的實質增量。這種實質增量的來源如果是最高人民法院認可的指導性案例固然最好,即使沒有成為或暫時沒有成為指導性案例,如其中有對既有規則的發展或進步,也值得學術界予以發掘和闡揚。這類具體的裁判規范本身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活法”,在民法學研究中可以作為解釋論的一部分,整合進入民法教義學體系。
最后,民法注釋書還應反映學者通說見解及其他見解(少數說)。在未形成通說的場合,更應該全面梳理既有學說觀點。比如圍繞《合同法》第64條規定的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利益第三人的合同),第三人是否享有直接請求債務人履行的權利,法條字面反映不清楚,學理解釋頗有分歧,很難說哪種學說算是通說。民法注釋書針對這種情形,就應當客觀梳理,是否可因此而促進通說的形成,亦未可知。
(四)民法注釋:已經做的、正在做的和應當做的
天下大事,必作于細。一步到位完成一部民法注釋書固然理想,就單個法條,按注釋民法的套路寫作注釋,亦是一條可行的路徑。從國內法學刊物上發表的情況看,已經出現了這類作品,且有逐漸增加的態勢。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在2017年3月15日的頒布,在陸續出版的各式民法總則釋義書中,也出現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陳更研究員主編、謝鴻飛、朱廣新副主編的《民法總則評注》,該書總計18位作者,均系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吉林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蘇州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上海財經大學、河南財產政法大學以及濟南大學的教學科研人員。該書總計140余萬字。其編寫力圖超越通常的法律釋義,而以法律評注為目標,逐條注釋《民法總則》。對每個法條,力求描述和提示其歷史由來、規范目的、規范含義、證明責任及其他問題。在作學 理闡釋的同時,兼顧裁判案例的梳理。總體而言,算得上是一部名副其實的法律評注,為中國法律評注的編寫開了一個好頭,值得充分肯定。當然,該書仍有其不足,比如由于編寫時間緊,部分內容尚顯簡單。在發揮釋義功能的同時,是否揭示了通說見解并兼顧其他學說,同時兼顧裁判立場,不同作者完成的程度不一。不過,萬事開頭難,該書已經開了一個好頭,為今后進一步的充實完善,打下了框架,奠定了堅實的工作基底。
除了上述已經做成的,正在做的也值得關注。據黃卉教授介紹,2013年8月在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法律系召開了第三屆中德民法論壇,就中德合作編纂中國法律評注的可能性達成了共識,由以澤克爾( Franz Jurgen Sacker)教授【《德國民法典慕尼黑法律評注》(第1卷)的主編】為首的德方教授提供智識及方法支持,由中方張谷、張雙根、朱慶育、田士永、王洪亮和黃卉等教授組成評注小組,以《合同法》為對象, “摸著石頭過河”,開始嘗試合同法評注的寫作。目前,此項工作仍在進行中。前文提及朱慶育等人的評注論文,可算是該評注小組的中間成果。
法律評注可大可小,小的可由一人執筆,比如德國學者揚·克洛弗勒( Von JanKropholler) -人為學生學習和考試使用而寫作的民法典評注;大的則必須集結作者團隊完成。在中國,大型民法評注工作無疑應當成為中國民法研究會或者中國法學會的一項重點工作,因為該研究會最具有團結舉國民法學人的能力。集眾學人之智慧,成偉大之法典評注。讓我們期待中國民法研究會或者中國法學會,在關注民事立法的同時,關注并積極推進大型民法評注的組織和開展工作.
摘自:《中國法律評論(2017年10月第5期.總第17期)》,法律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內容簡介:本期卷首語由著名法學家張晉藩教授題寫,題為《以史為鑒 可知興替》。五千年中華法文化歷史蘊藏著豐富的智慧和思維,作者梳理了自戰國至清代的監察思想、監察制度及監察法,提出以供借鑒的五點價值,或許對我國當下監察體制改革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淘寶鏈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0985676811
微店鏈接:https://d.weidian.com/item/#/add/edite?itemID=2194725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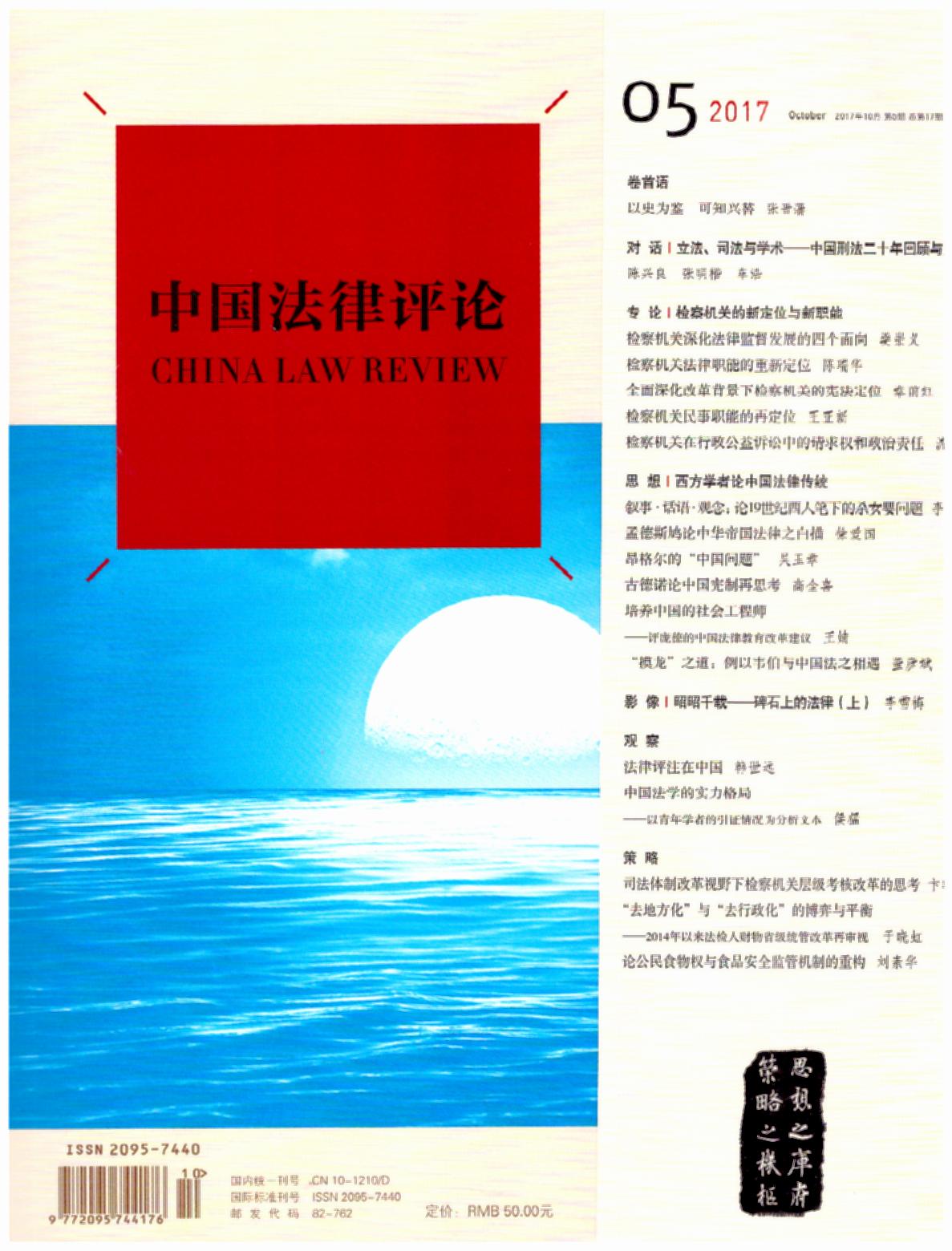 法律評注在中國
法律評注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