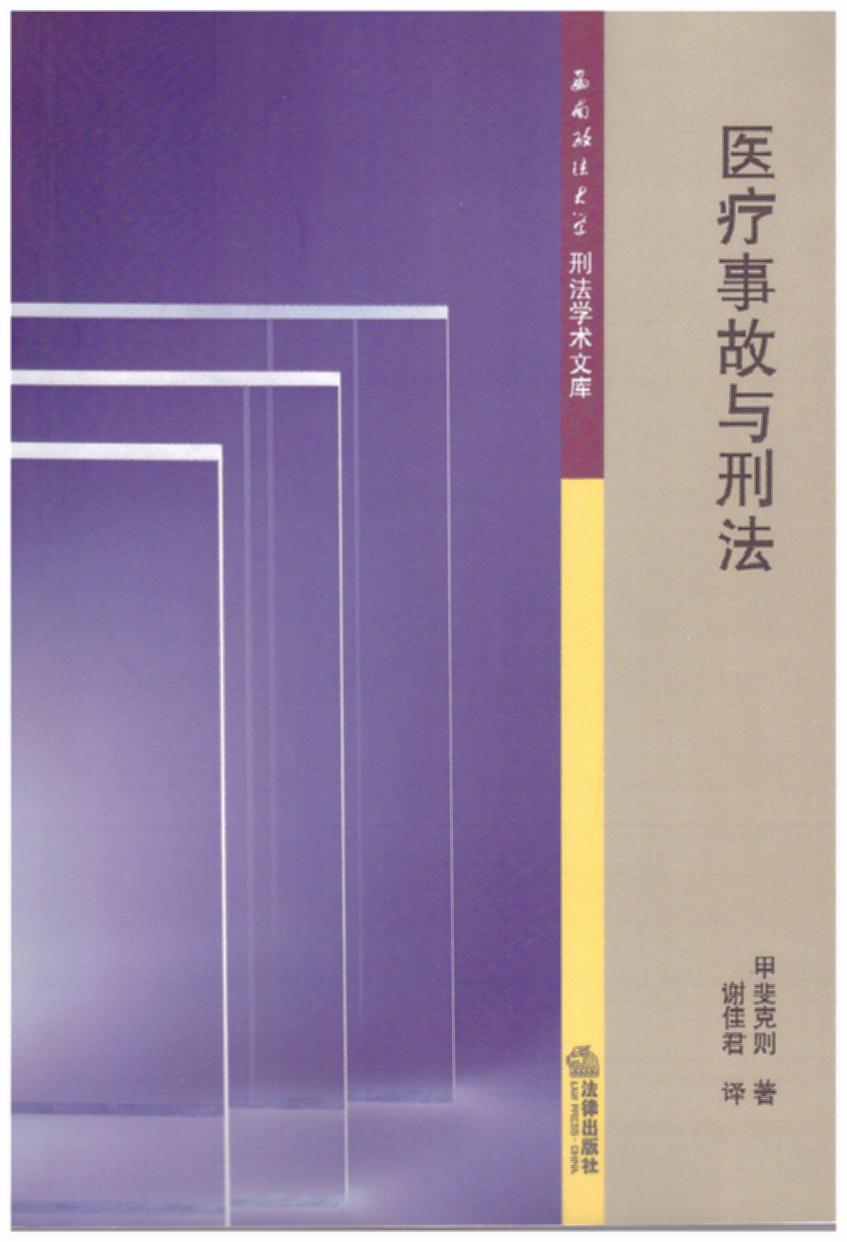
五、醫療事故的法律規制與風險管理
本學會是日本醫療。醫院管理學會,因此在這里筆者將對醫療事故的法律規制以及風險管理提出若干建議。風險管理也包含“廣義的風險管理”與“狹義的風險管理”,并分為好幾個階段。
第一,被害人之所以提起訴訟,從被害人的角度來說是因為他們想要了解事故發生的原因。如果盡早向被害人一方解釋是什么原因導致事故降臨到被害人的,那么大多數情況下都有利于其后的應對。這不僅僅限于醫療事故。初期的應對對于任何事情而言都很重要。若將初期應對拖延很久,則會導致被害人一方焦慮不安。對原因的解釋責任非常重要。第二,若責任歸屬已經明確清楚,則鄭重地道歉尤為重要。有醫療相關人員擔心一旦低頭道歉就意味著表明自己承認接受法律責任。但是并非如此,首先面對遭遇了事故的人肯定確實是在該醫院發生了該事故,不管各自道歉的具體內容是什么,也不管是否存在過失,首先表示歉意乃至關重要之舉。另外,如果是在已經明確認定為人為失誤的案件中,則在承擔解釋責任的同時也履行道歉義務,則有利于將事態往ADR解決的方向發展。換句話說,不
用進入訴訟階段便可了結案件。被害人一方也會認為院方已經表現出了誠意,因此不想把事情鬧得更大,也有可能出現放棄訴訟的心理。這不僅僅限于醫療事故,這是在大多數事故中都存在的一種人的心理狀態。第三,該事故的教訓可以為防止以后的醫療事故。被害人也對這一點很關心。這或許正是生命倫理的作用。正如美國正在進行的那樣,讓受害人一起參加事故防止對策,也是很好的。
接下來是醫療事故的報告義務問題。由于時間關系只論述相關要點(詳細內容請參見甲斐克則:“醫療事故的報告義務與風險管理”,載中山、甲斐編·前出《新版醫療事故的刑事判例》第290頁
以下)。此問題在都立廣尾醫院案中廣受關注。在都立廣尾醫院案中,院方在查明了患者因護理過誤引起的事故而死亡時,院長與主治醫師變更了當初的解決方針(向警察提交事故死亡報告),將病歷改寫為“病死”。除了篡改病歷,最終還因為沒有在24小時以內向所屬警察署提交報告,院長觸犯了《刑法》第155條第1項、第156條、第158條第1項所規定的偽造虛假死亡診斷書罪、偽造虛假公文書罪、使用偽造虛假的公文書罪以及《醫師法》第21條、第33條的違反非正常死亡報告義務罪而被判處有罪。最高法院提出:“通過尸檢發現死者乃非正常死亡的醫師,即使自己有可能因為其死因,使自己因診療行為中的業務過失致人死亡等被追究刑事責任,但其仍負有報告該案的報告義務,這并沒有違反憲法第38條第1款”,從其與不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之特權(拒絕證明自我入罪特權)的關系來看,
最高法院認為報告義務的規定并沒有違背憲法[最判平成16年(2004年)4月13日《刑集》第58卷第4號第247頁]。既然最高法院判例已對此作出了明確的判示,想必目前現行法也將按照此動向實行,但這是否合理呢?
接下來將簡單探討一下制度論、政策論的相關問題。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醫師法》第21條在現行法中是否合理的問題。該條“非正常死亡”的報告義務之規定具有以下立法背景,即原本是指對有可能卷入犯罪的死傷案中的被害人的非自然死亡進行報告。當然從形式上看,我們也不能否定因醫療過誤導致死亡的也包含在內。因此學界最近幾年一直在探討醫療關聯死的特殊規則問題。在立法論方面,筆者主張仍然應當在非正常死亡報告義務規定中對醫療關聯死設定例外規定。因為要探明死因究竟是由于純粹的醫療過誤引起的,還是并發癥引起的,其間糅雜著各種因素,要在24小時以內鎖定死者的死因在時間上并不是很充分。另外,若提出報告而使警察介入,警察也并不是該領域的專家,其實際處理起來也比較困難。因此筆者個人覺得應當需要對該條規定進行修改,但是問題是應當怎樣修改。也就是說,涉及什么范圍內的事故、由誰、什么時候、向哪里提交死亡報告等問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討論這一系列問題。另外,事故也包括死亡事故與尚未致死的事故。在日本外科學會制定的方針(2002年7月)中提出,不僅僅是死亡事故、在負傷階段都應當向警察報告。但該應對措施有些苛刻。因此,筆者建議應當向不是警察這樣的機關提交報告。目前正在試行向第三方機構提交報告,但其僅僅是過渡時期的政策,還尚不夠完善。
對于此問題我們可以參考新西蘭的制度。在新西蘭確立了醫療事故被害人補償系統。雖然也許因為新西蘭人口比較稀少的原因,但“行為人與被害人的和解”這一修復性司法乃新西蘭的傳統。幾
年前筆者曾做過調查,其設立有“醫療或殘障事務申訴委員會法”(Health and Disability Commissioner Act.HDCA 1994年),因此而設置了保障患者權利的獨立的公立機構“醫療或殘障事務申訴委員會”(Health and Disability Comnussioner,HDC)(參見本書第十二章)。該機構負責闡明醫療事故的原因。在發生了醫療事故時,該機構立即組成專家組前往現場,以找出事故的原因。該團隊中必須有1名法律家,其他成員均是與醫療相關的人。并且當確定是醫療者的過誤時,還會讓其對患者道歉。這也是一種ADR,即修復的手段之一。日本也可參考該制度。另外,不論是故意還是過失,都由事故賠償法人(Accident Compensation Corporation,ACC:國家獨立行政法人)對被害人進行補償。其主要特征在于該兩個機構有效地銜接共同應對事故。當然還存在確保財源等課題,但部分日本產科醫療已經設立了補償制度,在擴充該制度時可以參考新西蘭的制度。
六、結語——確立醫事審判制度之建議
最后建議確立醫事審判制度。現有的審判系統在面對醫療事故的法律規制時,無論從時間上還是人力上都顯得吃力。應當建立查明原因類型的獨立的醫事審判制度。從模型來看,例如海難審判所、
公平交易委員會、證卷交易委員會等。另外,在德國有醫師職業法院。根據國家的不同,需要在各方面下功夫。同時有必要早日實施被害人的救濟制度。例如上文所提到的賠償系統。另外,目前對醫療事故報告的機構雖然根據上述示例可以設立第三機構,但其界限也越來越明顯。對此我們可以設立一個新的報告機構,自治體與醫師會聯手,若要各都道府縣分別設立有些困難,或者全國可分為8個或者11個區域,在各個區域設置醫療事故報告機構,這也是一個方案。并同時成立醫事審判所,找出事故原因將會變得更快,同時也會加快被害人的救濟。對于其中“性質惡劣”的案件,可以對其保留采用以往糾紛處理方式的余地。其中要作為刑事案件來處理的則應當限定在具有“重大過失”。
另外,在今后的對策中,也應當考慮設立過誤過多的重復過誤者賦以進行研修的義務。據托馬斯野口先生說,“美國將醫師資格定期審查在同行審評中進行”。在日本要保證一定的質量,該制度也
可用來參考。但具體問題應當由醫療界的各位來進一步探討。
綜上所述,上述制度既可以在“廣義上的風險管理”又可以在針對眼前的“狹義上的風險管理”上得到靈活運用。另外還想強調一下“醫療與司法的橋梁”。我國現狀是目前這兩者之間還存在很大
的間距。當案件進入審判階段時,法官僅靠短時間的學習便承擔醫療問題,這顯然不夠。在東京等地的法院成立了醫療專門部,該制度值得好評,但仍然不夠。我們有必要考慮創造醫療關系人與司法、法律關系人日常工作中充分、緊密的情報交換以及意見交換機會。2009年筆者赴荷蘭調查的時候,格羅寧根大學醫院將其付諸實踐。在日本,千葉縣鴨川市的龜田綜合醫院便雇傭年輕律師作為醫院職
員,以此來應對,希望此類醫院逐步增加。這與其叫作“醫療與司法的橋梁”,也可以說是風險管理的方針之一。
摘自:《醫療事故與刑法》P27-31頁,法律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內容簡介:近年,醫療事故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醫療事故”與“醫療過誤”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以往要追究醫療過誤的法律責任,一般將重點放在從某一方面特定某個人,即采用“個人模式”,但是,最近學界將焦點集中在了“組織模式”上。《醫療事故與刑法》通過日本近期發生的代表案例出發,在深入研究了醫療事故與刑法的界定問題的同時,提出了建立醫療事故的被害人救濟系統等建議。
淘寶鏈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50380995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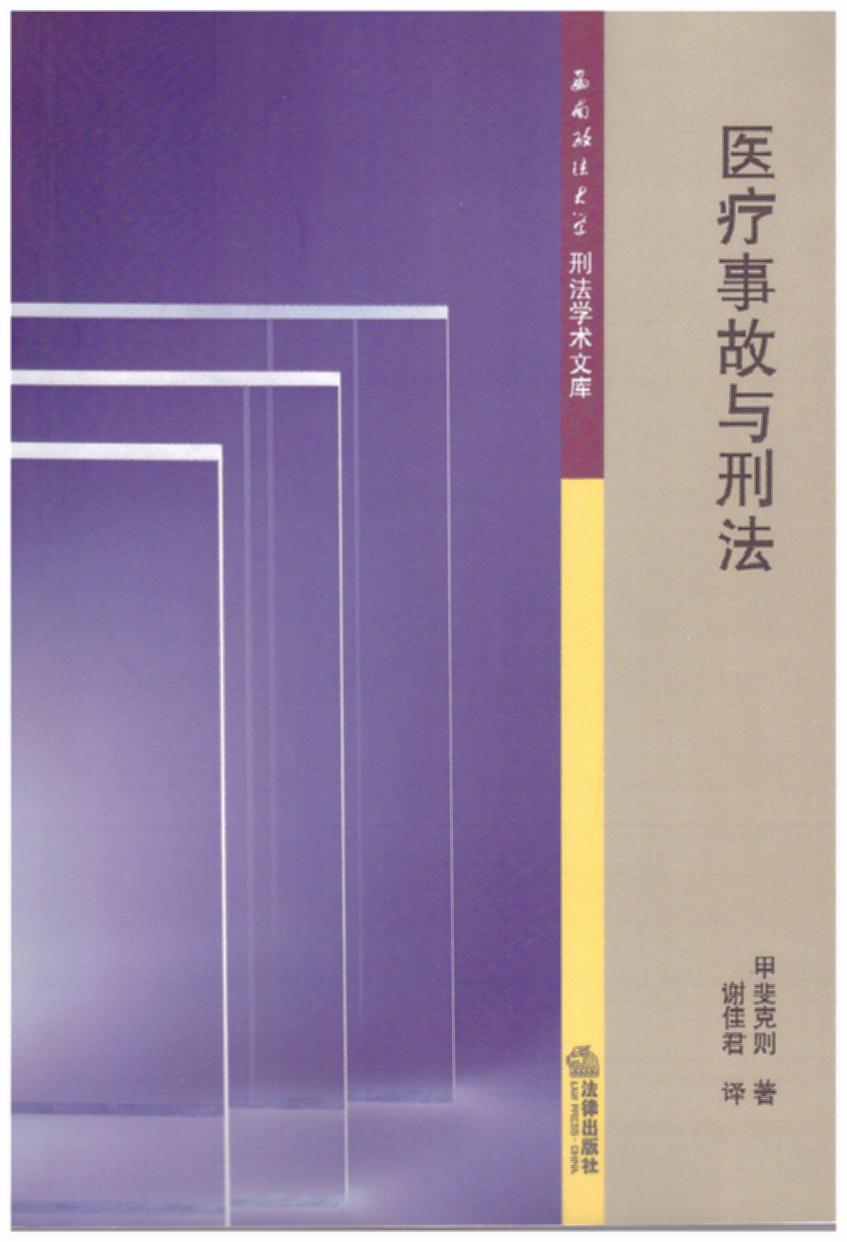 五、醫療事故的法律規制與風險管理
五、醫療事故的法律規制與風險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