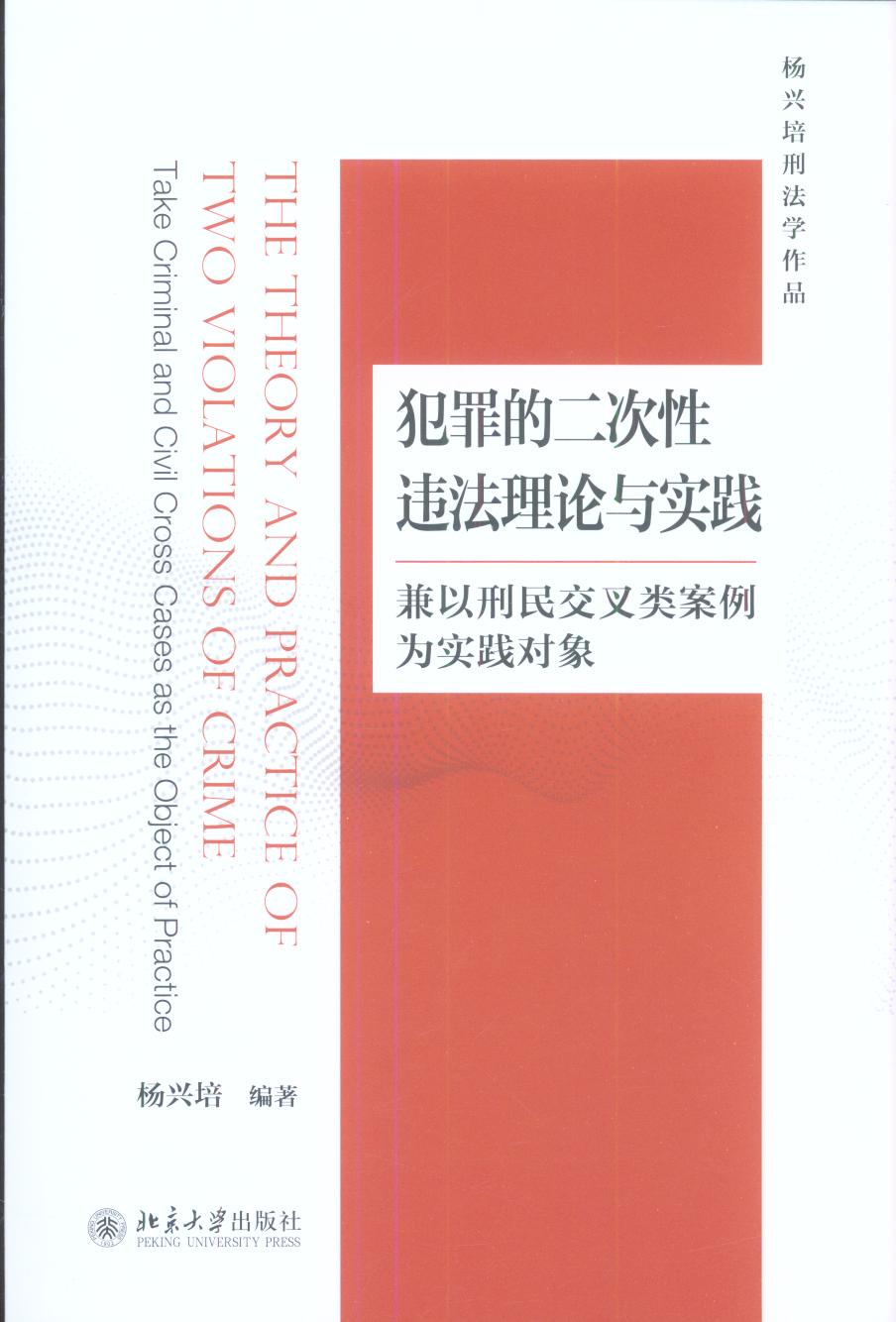
一、基本案情介紹
在目前經濟犯罪的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大量的刑民交叉現象。如何正確處理這一類犯罪并較好地理順與民事法律關系的區別,是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筆者以下面這一案例為例,試圖提供破解邃一難題的邏輯進路。
2008年初,龔某因賭博對外欠債,遂與其友丁某共謀想私下出售龔父名下的一處房產以還賭債。經預謀,同年8月,龔某先取其家中戶口薄向公安機關以身份證遺失為名補辦龔父的身份證。第二步,龔某持其父身份證向房產登記部門辦理產權證掛失登記,并補辦房屋產權證。第三步,龔某持補辦的其父身份證和房屋產權證,化妝后冒充其父親,與丁某共同至公證機關委托丁某出售房屋,騙得委托公證文書。經房產中介介紹,丁某于2008年10月6日,持上述虛假委托公證書,以及龔某交付的其父身份證、房產證,與王某簽訂房地產買賣合同。同時丁某還持龔父的身份證至建行開戶,并以此賬戶收取并占有了買方的購房款43萬余元。后丁某將相關房產過戶至王某名下。所獲錢款揮霍一空。該案的情節還有:從龔某身份證上的照片來看龔某與其父相差無異,容易讓人誤以為龔某就是其父親本人,事實上王某的確陷入認識錯誤;從出示給王某驗看的身份證、房產證、公證文書都是真實的,王某有充分理由相信這一買賣就是龔某父親本人的真實意思表示;龔父發現房屋被賣后向公安機關報案。龔父事后向法院起訴根本不承認這一買賣的合法性,堅決要求收回屬于其本人的房產。
二、判決結論、問題的提出及筆者的疑惑
經過刑事訴訟,人民法院最后以合同詐騙罪判處被告人龔某與丁某二人有期徒刑的刑罰,同時判決中還把本案的王某確定為被害人,其判決內容之一為:“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予追繳后發還被害人。”刑事判決生效后,龔父向法院起訴房屋買受人王某,主張房屋買賣合同無效、王某應退還房屋,并以該判決書為主要證據。王某一邊打民事官司,一邊向檢察機關提出刑事申訴。王某主張:其本人為善意第三人,依法應取得該房屋產權,其并未被騙,原刑事判決將其認定為被害人是錯誤的。
《政治與法律> 2011年第11期發表了吳加明的文章——《合同詐騙罪與表見代理之共存及其釋論——一起倒賣房屋引發的刑民沖突及釋論》一文,文中就該案提出了作者的鮮明觀點,支持該案應當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因此無論從法院的判決來看還是吳文的基本觀點來看,都是把本案看成是一起合同詐騙罪。
筆者細細品味該案,認為上述判決在刑法理論上存在著諸多的瑕疵。筆者對這一類型刑民交叉案件情有獨鐘,認為對其中一個案件的“解剖麻雀”,也能起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效果,這對刑法理論展開深入研究甚至對刑法的經典教學也大有裨益。為此,筆者就這一類案例進行深入研究,以求澄清一些刑法理論的是非,也以此促進對這一類案件的正確認定。
從本案的基本案情來看,龔某與王某的房屋買賣屬于一種表見代理,因此王某通過龔某的表見代理獲得龔父房產的所有權是一種“善意取得”。但能否因龔某瞞著其父與王某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就可以認定龔某構成合同詐騙罪,從而形成刑法語境下的“合同詐騙”,進而與民事法律中的“善意取得制度”發生沖突,并由此引發刑民交叉與刑法上的被害人如何定位等一系列問題,這都有待于我們的深入討論。
根據民法的規定,合同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雙方當事人為確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而簽訂的一種協議;而根據刑法的規定,合同詐騙罪是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手段,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錢財的行為。合同詐騙罪基于合同行為而產生、而成立。因此,合同詐騙的行為人必須是合同的一方當事人,而合同詐騙罪的被害人也必須是合同的相對方當事人,這是刑法明文規定的確切內容。如果龔某的行為可以構成合同詐騙犯罪,那這一合同詐騙罪的被害人必定是購房者王某,原先的房屋買賣合同必然屬于無效合同。這是就刑法理論與刑法實踐而言的。但是如果就民法理論與民法實踐而言,無效合同的法律效果從其一開始就為無效,雙方必須各自返還財物,無過錯且受損失一方有權要求賠償。如果在合同簽訂和履行過程中,他人基于某種合理合法的現象而善意取得他人的財產,即使發生刑事犯罪,法律也應當承認善意取得的合法所有權。民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通常的理解是,無處分權人把他人的東西予以出售、交易,而購買方在買賣交易過程中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其出售的財物是他人真實意思的表示,并且支付了合理的相當于市價的款項,這樣即使真正的財產所有人蒙受損失,想要恢復財物原狀,但法律還是出于交易安全、交易穩定考慮依然保護善意取得人的所有權。正如《合同法》第49條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這就是民法上的表見代理,其意義在于維護代理制度的誠信基礎,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建立正常的民事流轉秩序。《物權法》頒布以后,不動產也采用了善意取得制度,最顯著的特征表現為物權和債權相分離,即使房屋買賣的合同被判無效,但原先的房屋買賣基于物權的公示、公信原則并已經登記過戶的,法律還是承認購買人取得的不動產所有權。通過這樣的民法考察,合同詐騙與善意取得制度并不矛盾,就算是因為合同詐騙而使原房屋買賣合同無效,但由于物權和債權可以分離,善意購買人依舊可以取得房屋所有權。
然而在刑民交叉的刑事案件處理過程中,確定誰是被害人有時則使兩者的關系發生根本的變化,甚至會導致案件出現意想不到的邏輯錯誤:將合同相對方作為被害人,這是絕大多數合同詐騙案件的通常做法,在司法實踐中也無多大爭議。然而在本案中,由于合同相對方作為善意第三人,法律保護他的合法權益,他已實際轉變成了本案房產的合法所有人,此時再將他認定為“被害人”顯然不妥。因為本案中此時的王某根本沒有“被害”,善意取得制度正在保護著他,房子已經屬于他,他沒有遭受到任何損失。也正因為此王某向司法機關提出申訴,不承認自己是“被害人”。而法院一旦將他確定為案件被害人,通常的做法是被告人(行騙方)取得的違法所得應如數退還給被害人,這也是本案刑事判決的內容。這樣的后果使合同相對人王某既能獲得房屋所有權又能把之前被“騙”的錢款要回來,相當于賺到“雙份利益”,本案的刑事判決“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予追繳后發還被害人”即是如此(雖然錢被揮霍一空已無執行的可能性),這顯然有違法律規定和法理原理。而龔父提起民事訴訟想要恢復房產原狀,障礙就更大了。房屋已屬于王某,而且有刑事判決書作為依據,因而民事處理甚是為難。②如果將房產的原先所有人作為本案合同詐騙罪的被害人,也就是龔父,因為真正受害的也的確是龔父。可是將原先的房產所有人作為被害人也有問題。首先,合同詐騙罪的前提是合同關系的存在,合同詐騙罪的法定被害對象為簽訂合同的對方當事人,而本案中的房產原所有人并沒有參與簽訂合同,將其作為被害人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規定。其次,刑事詐騙的核心含義就在于受害人基于錯誤的認識而作出一定的交付行為。但本案中房產的原所有人既沒有產生什么錯誤的認識,也沒有作出與此相關的行為表示。由此看來,要將龔父認定為本案合同詐騙罪的被害人沒有法律根據。再次,如果將龔父認定為被害人,相應的法律后果是使房屋回歸到原始狀態,即回歸到真正的所有人名下,合同一方被騙的錢款退回給被騙的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對方當事人,但這樣又會違反民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造成刑法與民法的明顯沖突。進一步而言,如果將房屋歸還給房屋原所有人的話,那么從民法的角度來看,房屋交易就變得極不安全。這是因為在正常的房屋買賣過程中,在第三人完全沒有惡意、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他人進行交易,當對方出示的證明文件、產權證件等均為真實、合法、有效,還要其關注合同交易過程中的其他非法律規定的因素,那么任何一樁房屋買賣交易還能正常進行嗎?所以,無論把,都無法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這些問題的存在都使得本案變得格外復雜,需要進行深入的探討。
摘自:《犯罪的二次性違法理論與實踐:兼以刑民交叉類案例為實踐對象》P260-263頁,北大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內容簡介:法治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在于如何培固刑法前置性法的根基,在于樹立作為刑法前置性法的權威性,在于首先由刑法的前置性法對社會進行有效的分兵管控。如果沒有其他法律作為刑法的前沿屏障,沒有刑法的前置性法分領域、分層次、分程度地對不同類型的危害行為適用不同的法律制裁,而將其大小不同的違法危害行為全部納入刑法調整的范圍,一味動用刑罰手段,既不是一個明智的作法,也必然面臨捉襟見肘的困境。所以我國在進行法治化建設過程中千萬不能本末倒置,不然法治目標只會緣木求魚而不可得也。本書為了從司法實踐中獲得理論的原料和營養而展開對一些刑法基礎理論和刑民交叉案例的思考和討論,也可供司法工作人員在進行刑民交叉案例分析時作為一種參考系數和觀照尺度加以對照,從中找到可以吸收和借鑒的成分,或者從證偽的角度避免重蹈覆轍。
淘寶鏈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38n.10677092.0.0.1e3c1debyz1TMF&id=569088129249
微店鏈接: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25287600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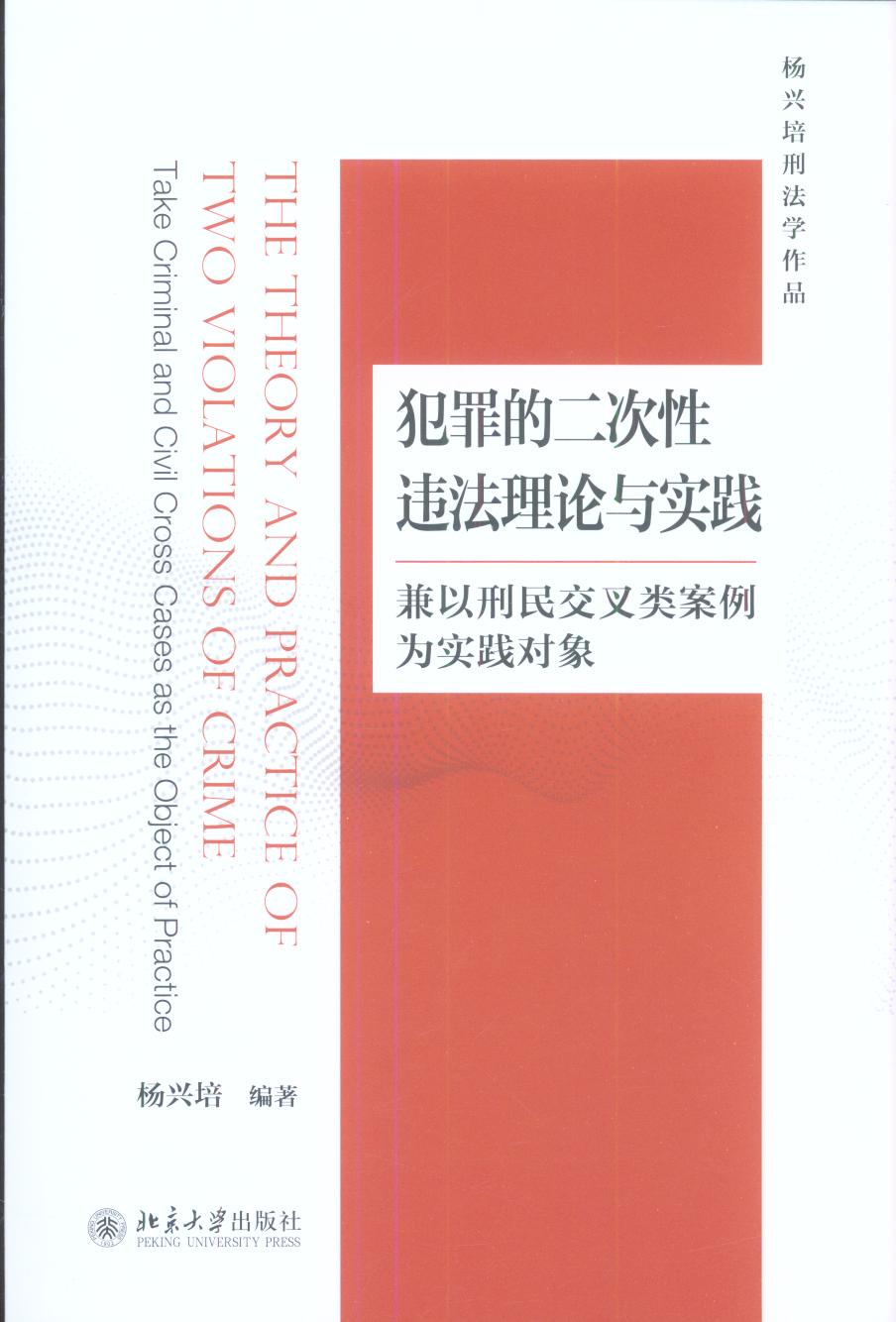 一、基本案情介紹
一、基本案情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