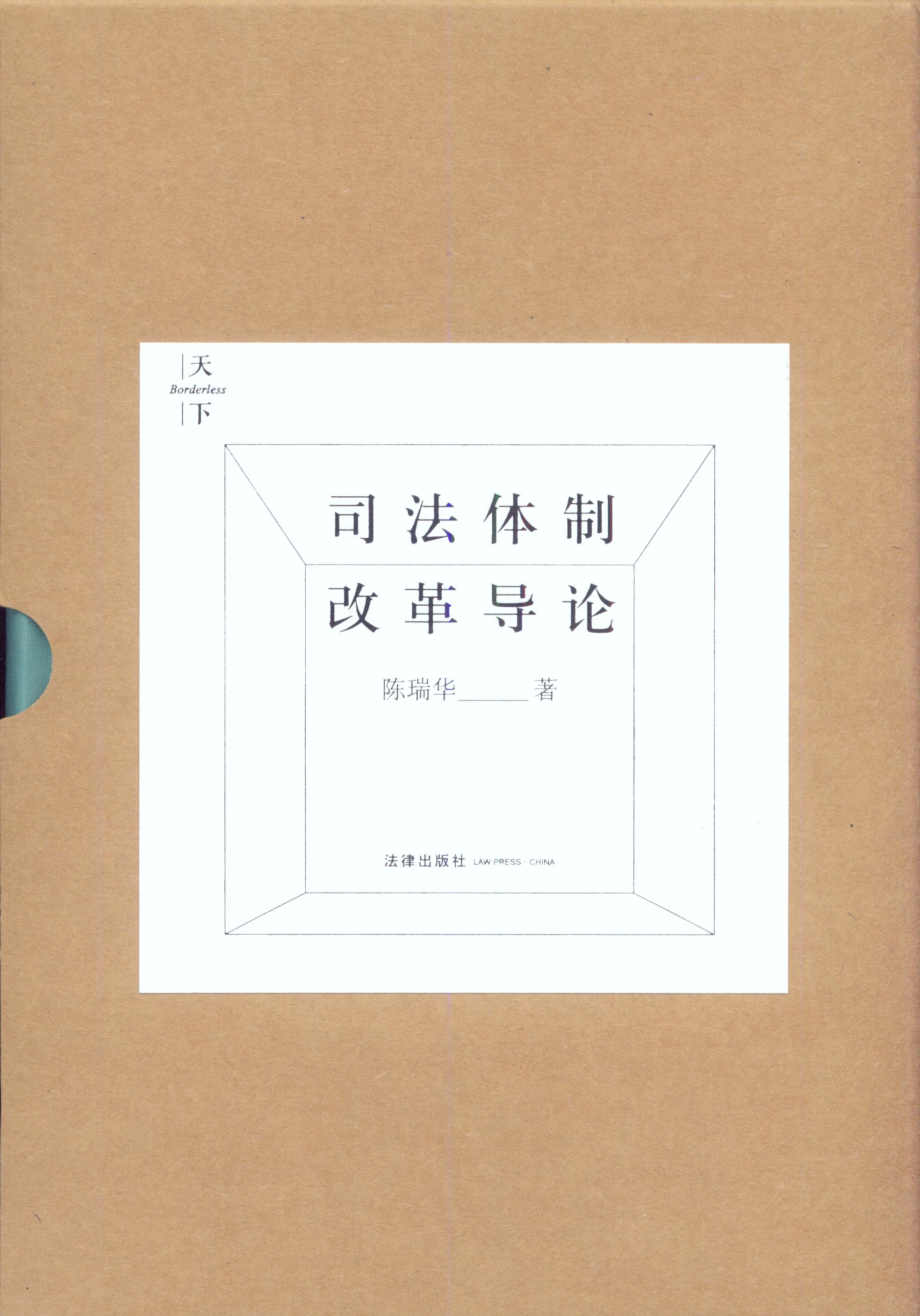
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就必須確保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有效的辯護。為此,至少應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獲得律師辯護的機會,對那些無力委托辯護律師的嫌疑人、被告人,應當盡可能指定法律援助律師提供辯護。應當說,最高人民法院會同其他部門通過的“意見”對完善辯護制度給予了強調。例如,《意見》重申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獲得辯護的權利,保障辯護律師的各項訴訟權利,強調完善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制度。但總體來說,改革決策者對于辯護制度的改革缺乏真正的重視,對于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有效辯護的機會沒有作出實質性的制度創新。
其實,我國現行刑事司法體制的最大問題在于,偵查機關對案件事實所作的認定結論,通過檢察機關的提交,可以暢通無阻地抵達法院,并成為法院裁判的直接依據。這種由公檢法三機關以“接力比賽”的方式所進行的刑事訴訟活動,最終導致偵查成為刑事訴訟的中心階段,審查起訴和審判都成為對偵查工作進行拾遺補闕和程序補救的后續活動。而要破除這種偵查中心主義的構造,除了要維護法院審判的獨立性和權威性以外,還需要構建一種強大的辯護方,足以對偵查機關移交的案卷筆錄及其所認定的事實結論形成有力的制衡。在沒有辯護律師參與或者辯護律師參與范圍極其有限的情況下,法院總有直接接受公訴方案卷材料及其認定事實結論的傾向,既無法將偵查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排除于法庭之外,也無法拒絕偵查機關庭前業已形成的事實認定。一言以蔽之,不確保被告人獲得有效的辯護,審判中心主義改革將是無法完成的。
要確保被告人獲得有效的辯護,就至少需要擴大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目前,強制性法律援助主要適用于那些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案件以及其他三類特殊刑事案件。這種法律援助適用范圍極其有限,導致大多數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無法獲得律師的法律幫助。就連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沈德詠都承認,在那些沒有辯護律師參與的案件中,辯護方“無法與控方形成有效的抗衡,庭審的效果大打折扣”,要實現庭審實質化,擴大法律援助適用范圍勢在必行。
要確保被告人獲得有效的辯護,就需要在推廣值班律師制度的基礎上,對其進行“辯護人化”的制度改造。目前,我國已經普遍在看守所和法院分別設置法律援助值班律師辦公室,為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特別是在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過程中,幾乎所有愿意認罪認罰的嫌疑人、被告人都有機會獲得值班律師的幫助。但是,這種值班律師制度存在一些先天的缺陷,亟待進行“辯護人化”的改造。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值班律師適用范圍也是十分有限的,很多偵查機關和法院主要對那些自愿認罪的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值班律師的幫助,但那些既不符合指定辯護條件又不愿認罪的嫌疑人、被告人,卻很難獲得值班律師的幫助。這帶有明顯的“懲罰不認罪者、獎勵認罪者”的意味。二是值班律師主要為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詢,其本身并不是辯護人,既無法行使會見、閱卷、調查等訴訟權利,也無法在法庭上為被告人提出辯護意見,這導致公訴方的指控難以受到有效的制衡,法官也無法了解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和法律適用意見。
在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獲得律師辯護的前提下,我們還需要通過制度安排來督促律師提供盡職盡責的辯護。有效辯護并不等于達到某種訴訟結果的辯護,而主要是指律師恪盡職責,找準找對了案件的辯護思路,并盡最大努力為委托人提供了法律幫助,維護了委托人的合法權益。要督促律師進行有效的辯護,就要建立兩種機制:一是對盡職盡責律師的激勵機制;二是對無效辯護律師的懲戒機制。激勵機制可以主要通過改革律師收費制度來確立起來,改革現行的“一攬子收費制度”,逐步推行根據工作量來收取費用的制度,以使那些盡職盡責的律師獲得更多的報酬。而懲戒機制則可以分為訴訟程序內的懲戒和訴訟程序外的懲戒兩類,前者是指對于律師作無效辯護的,二審法院應當以被告人無法獲得有效辯護為由,作出撤銷原判、發回重新審判的裁定。后者則是指對于無效辯護的律師應確立懲罰性法律后果,由律師懲戒機構對其進行紀律處分。
但是,要確保被告人獲得有效的辯護,僅僅督促律師盡職盡責地提供辯護還是遠遠不夠的。在一個不盡如人意的制度下,一個律師即便為維護委托人的利益付出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也未必能夠提供令人滿意的法律幫助。律師的有效辯護還取決于司法體制和訴訟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律師辯護的機會。在審判階段,對于辯護律師申請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專家輔助人出庭作證的,法庭動輒以“沒有必要”為由,拒絕了律師的申請;對于辯護律師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法庭通過粗糙的調查就直接加以拒絕,甚至非常草率地拒絕啟動正式調查程序;對于辯護律師申請二審法院開庭審理的,二審法院不經認真審查,就直接加以拒絕,而采取書面審理方式……法院這種濫用自由裁量權的審判行為,直接導致律師失去辯護的機會,也進而導致無效的辯護。
在審判前階段,辯護律師即便能夠介入刑事訴訟活動,其參與范圍也是極其有限的。迄今為止,律師在審判前階段的辯護充其量也只是向偵查人員、審查批捕的檢察官以及審查起訴的檢察官發表或者提交辯護意見而已。而在大量使嫌疑人處于極為危險境地的訴訟過程中,法律都禁止律師參與其中,更遑論提供辯護了。例如,在偵查人員訊問嫌疑人過程中,律師被禁止到場參與,這導致訊問過程很容易出現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現象;在勘驗、檢查、搜查、扣押、凍結、拍賣、辨認、偵查實驗等強制性偵查過程中,律師被禁止到場,失去了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機會;在偵查人員啟動鑒定程序過程中,律師也被禁止參與其中,失去了對鑒定活動進行必要參與的機會……經驗表明,在任何可能導致嫌疑人、被告人處于不利境地的訴訟活動中,只有給予辯護律師參與的機會,才能避免偵查機關實施違反法律程序的行為,避免檢察機關濫用公訴權,避免法院偏聽偏信,以至于作出錯誤或者不公正的裁判。
摘自:《天下·司法體制改革導論》P410-413頁,法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內容簡介:本書分三個部分,分別討論了司法改革的宏觀問題、法院改革問題以及公檢法三機關的法律關系問題。在本書第一部分,筆者討論了司法權的性質,對法院改革的兩個理論基點進行了反思,并對檢察制度、司法行政制度的改革進行了分析、評論和預測。在第二部分,本書分析了我國法院改革所面臨的困境,結合司法責任制的推行,提出并分析了法官責任制度的三種模式,結合審判委員會制度、承辦人制度以及合議制的運行實踐,反思了司法裁判的行政化問題,并預測了司法行政管理與司法裁判職能的分離問題。在第三部分,本書圍繞著“審判中心主義”和“庭審實質化”改革問題,反思了我國公檢法三機關的“流水作業”模式,分析了我國存在多年的“偵查中心主義”訴訟構造,討論了未曾受到觸及的“新間接審理主義”模式,還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運行效果為范例,全面評論了我國刑事訴訟的縱向構造模式。考慮到改革決策者特別強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重要性,并將其適用范圍擴展到那些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因此,本書對這一制度進行了理論上的反思,討論了刑事訴訟權利全流程簡化的改革問題。
淘寶鏈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38n.10677092.0.0.11891deblvhCGC&id=571065066709
微店鏈接: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2549235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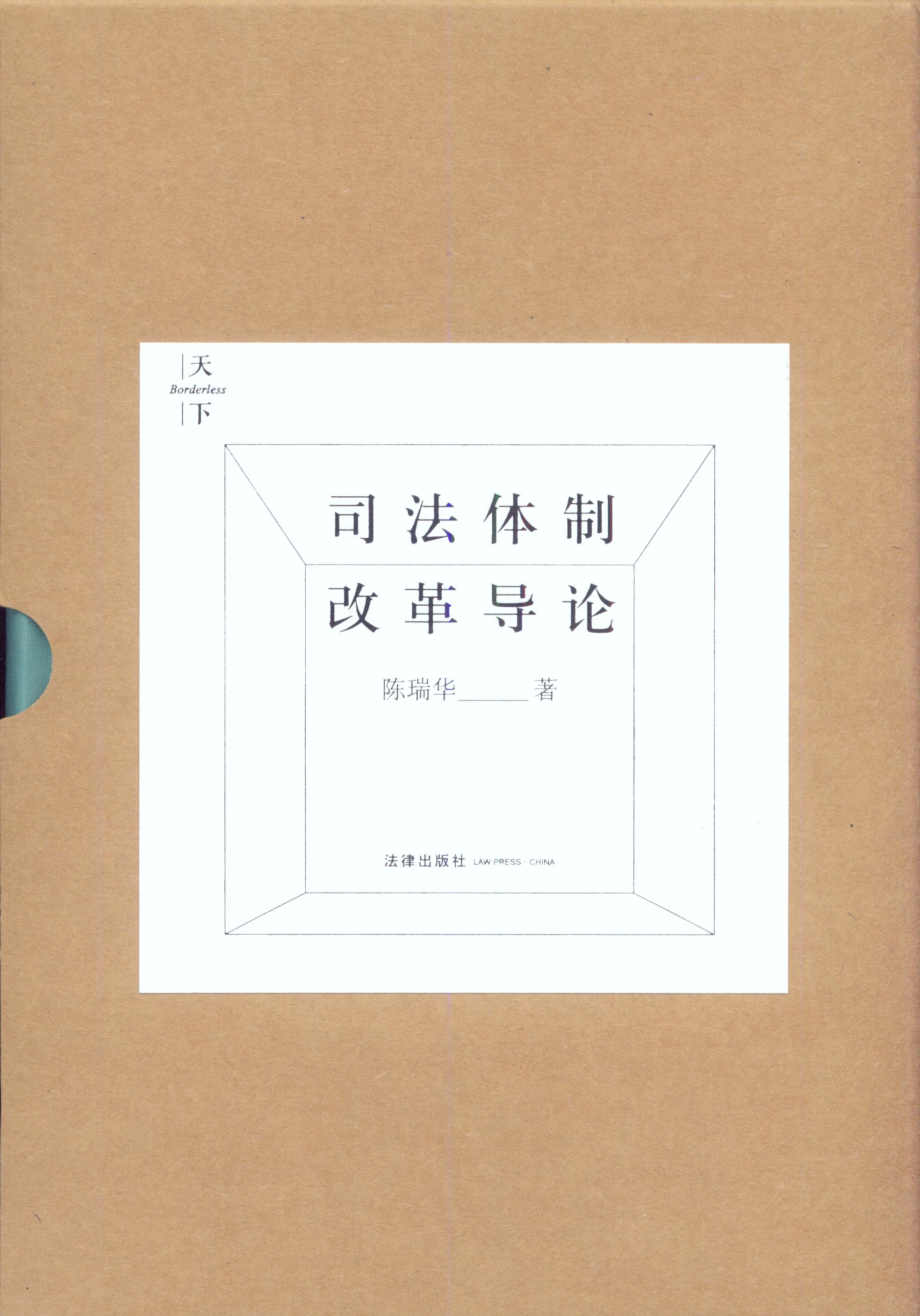 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就必須確保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有效的辯護。為此,至少應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獲得律師辯護的機會,對那些無力委托辯護律師的嫌疑人、被告人,應當盡可能指定法律援助律師提供辯護。應當說,最高人民法院會同其他部門通過的“意見”對完善辯護制度給予了強調。例如,《意見》重申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獲得辯護的權利,保障辯護律師的各項訴訟權利,強調完善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制度。但總體來說,改革決策者對于辯護制度的改革缺乏真正的重視,對于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有效辯護的機會沒有作出實質性的制度創新。
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就必須確保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有效的辯護。為此,至少應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獲得律師辯護的機會,對那些無力委托辯護律師的嫌疑人、被告人,應當盡可能指定法律援助律師提供辯護。應當說,最高人民法院會同其他部門通過的“意見”對完善辯護制度給予了強調。例如,《意見》重申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獲得辯護的權利,保障辯護律師的各項訴訟權利,強調完善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制度。但總體來說,改革決策者對于辯護制度的改革缺乏真正的重視,對于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有效辯護的機會沒有作出實質性的制度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