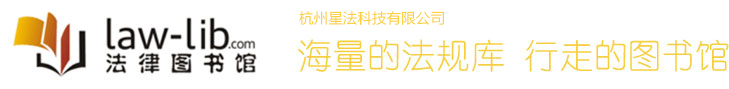寬嚴(yán)相濟(jì) 重在轉(zhuǎn)化 最大限度發(fā)揮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優(yōu)勢(shì)
——最高檢第九檢察廳負(fù)責(zé)人就第二十七批指導(dǎo)性案例答記者問
3月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fā)布第二十七批指導(dǎo)性案例(“對(duì)涉罪未成年人附條件不起訴”主題),最高檢第九檢察廳廳長(zhǎng)史衛(wèi)忠就相關(guān)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
記者:什么是附條件不起訴?適用附條件不起訴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史衛(wèi)忠: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二條規(guī)定,對(duì)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規(guī)定的犯罪,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符合起訴條件,但有悔罪表現(xiàn)的,檢察機(jī)關(guān)可以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
從這個(gè)規(guī)定可以看出,適用附條件不起訴需要同時(shí)滿足以下幾個(gè)條件。一是適用對(duì)象是未成年人,成年人犯罪不能適用。對(duì)實(shí)施犯罪行為時(shí)系未成年人但訴訟過程中已滿十八周歲的犯罪嫌疑人,符合條件的也可以適用。牛某非法拘禁案就是這樣一個(gè)例子。二是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規(guī)定的犯罪,即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權(quán)利、民主權(quán)利罪,侵犯財(cái)產(chǎn)罪、妨害社會(huì)管理秩序罪的可以適用,其他類型犯罪比如危害國(guó)家安全、公共安全、破壞社會(huì)主義經(jīng)濟(jì)秩序等犯罪不能適用。三是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是指可能的宣告刑,而非法定刑,即,如果將犯罪嫌疑人交付審判,法院對(duì)其可能判處的刑罰。比如,我們發(fā)布的胡某某搶劫案,搶劫犯罪法定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根據(jù)各種量刑情節(jié),調(diào)節(jié)基準(zhǔn)刑后測(cè)算胡某某可能判處有期徒刑十個(gè)月至一年,因而適用了附條件不起訴。還有,發(fā)布的李某詐騙、傳授犯罪方法、牛某等人詐騙案,李某雖觸犯兩罪,但綜合全案事實(shí)、社會(huì)調(diào)查情況以及犯罪后表現(xiàn),依據(jù)有關(guān)量刑指導(dǎo)意見,李某的綜合刑期應(yīng)在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因而也對(duì)其附條件不起訴,都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四是符合起訴條件。對(duì)于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二款規(guī)定的不起訴條件,也就是說,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屬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依照刑法規(guī)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條件的,應(yīng)直接依法適用不起訴,不能以附條件不起訴代替不起訴。五是有悔罪表現(xiàn)。《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指引(試行)》列舉了幾種情形,主要包括認(rèn)罪認(rèn)罰,向被害人賠禮道歉、積極退贓、盡力減少或者賠償損失,取得被害人諒解,具有自首或立功表現(xiàn),犯罪中止,等等。
總之,具備以上五個(gè)條件,檢察機(jī)關(guān)可以適用附條件不起訴,但這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實(shí)踐中有一些符合這些條件,但因幫教條件不具備等原因而沒有被附條件不起訴。今后,我們將繼續(xù)指導(dǎo)各地依法積極適用附條件不起訴,合理提高附條件不起訴適用率,更好地發(fā)揮這一制度的作用。
記者:對(duì)未成年人附條件不起訴的監(jiān)督考驗(yàn)期限是如何設(shè)置的?是否可以調(diào)整?
史衛(wèi)忠:對(duì)符合條件的涉罪未成年人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規(guī)定,需要設(shè)置六個(gè)月到一年的考驗(yàn)期,考驗(yàn)期的長(zhǎng)短要與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性質(zhì)、情節(jié)和主觀惡性大小相適應(yīng)。在此期間,被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人要遵守相關(guān)規(guī)定,并按照檢察機(jī)關(guān)的要求接受矯治和教育。檢察機(jī)關(guān)將根據(jù)社會(huì)調(diào)查情況,針對(duì)涉罪未成年人的具體犯罪原因和回歸社會(huì)的具體需求等設(shè)置附帶條件。考驗(yàn)期間,未成年人實(shí)施新的犯罪或者發(fā)現(xiàn)漏罪、違反治安管理規(guī)定或者檢察機(jī)關(guān)所附條件情節(jié)嚴(yán)重的,將撤銷附條件不起訴決定,依法提起公訴。唐某等人聚眾斗毆案就是因違反考察機(jī)關(guān)附條件不起訴的監(jiān)督管理規(guī)定被撤銷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后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個(gè)月。考驗(yàn)期間沒有上述情形,考驗(yàn)期滿的,檢察機(jī)關(guān)將依法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其余4個(gè)案例就是這樣的情況。
當(dāng)然,考驗(yàn)期限并非一成不變。檢察機(jī)關(guān)可以根據(jù)被附條件不起訴人的不同情況和個(gè)性需求,動(dòng)態(tài)調(diào)整考驗(yàn)期限和幫教內(nèi)容。比如,發(fā)布的胡某某搶劫案,鑒于胡某某表現(xiàn)良好、考上大學(xué)后角色轉(zhuǎn)變等情況,檢察機(jī)關(guān)組織家長(zhǎng)、學(xué)校、心理咨詢師、社區(qū)召開“圓桌會(huì)議”聽取各方意見。經(jīng)綜合評(píng)估,各方一致認(rèn)為原定考驗(yàn)期限和幫教措施已不適應(yīng)當(dāng)前教育矯治需求,有必要作出調(diào)整。檢察機(jī)關(guān)決定將胡某某的考驗(yàn)期縮短為八個(gè)月。同樣,根據(jù)教育矯治需要,檢察機(jī)關(guān)也可以決定延長(zhǎng)考察期限。
記者:“按照考察機(jī)關(guān)的要求接受矯治和教育”具體指什么?
史衛(wèi)忠:按照考察機(jī)關(guān)的要求接受矯治和教育,是指被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人要按照人民檢察院的要求接受一系列的矯治和教育項(xiàng)目,主要包括:(一)完成戒癮治療、心理輔導(dǎo)或者其他適當(dāng)?shù)奶幱龃胧?(二)向社區(qū)或者公益團(tuán)體提供公益勞動(dòng);(三)不得進(jìn)入特定場(chǎng)所,與特定的人員會(huì)見或者通信,從事特定的活動(dòng);(四)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五)接受相關(guān)教育;(六)遵守其他保護(hù)被害人安全以及預(yù)防再犯的禁止性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第四百七十六條對(duì)此作了明確規(guī)定。
從上述規(guī)定看,矯治和教育項(xiàng)目可大體分為四類,一是矯正類,如接受心理輔導(dǎo)、參加公益活動(dòng)、接受相關(guān)教育等;二是修復(fù)類,如賠禮道歉、損害賠償?shù)?三是限制類,如限制進(jìn)入特定區(qū)域等;四是保護(hù)觀察類,如戒癮治療等,并規(guī)定了一個(gè)兜底條款,即“(六)遵守其他保護(hù)被害人安全以及預(yù)防再犯的禁止性規(guī)定。”也就是說,檢察機(jī)關(guān)可以根據(jù)未成年人的具體情況和幫教需求來設(shè)置考察幫教的內(nèi)容,以保證取得預(yù)防被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促進(jìn)其健康成長(zhǎng)的實(shí)效。
記者:如果被害人不同意檢察機(jī)關(guān)對(duì)涉罪未成年人附條件不起訴,檢察機(jī)關(guān)可以作出附條件不起訴嗎?如何保護(hù)被害人的利益?
史衛(wèi)忠: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二條的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在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以前,應(yīng)當(dāng)聽取被害人的意見,如果被害人對(duì)人民檢察院作出的附條件不起訴決定不服,可以在收到?jīng)Q定書后七日以內(nèi)向上一級(jí)人民檢察院申訴。也就是說,刑事訴訟法賦予了被害人對(duì)附條件不起訴的程序參與權(quán),以及通過申訴尋求救濟(jì)的權(quán)利,但其意見及申訴在法定層面不具有阻斷附條件不起訴決定的效力,即使被害人不同意,檢察機(jī)關(guān)依然有權(quán)從教育、感化、挽救出發(fā),對(duì)涉罪未成年人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但是,在實(shí)踐中,檢察機(jī)關(guān)對(duì)被害人的意見非常重視,一方面是因?yàn)楸缓θ耸鞘芊缸镄袨榍趾Φ娜?在訴訟中是一方當(dāng)事人,而檢察機(jī)關(guān)負(fù)有維護(hù)當(dāng)事人合法權(quán)益的職責(zé)。被害人的意見對(duì)于檢察機(jī)關(guān)而言非常重要,如果沒有特別充分的理由,被害人意見檢察機(jī)關(guān)一般是采納的。另一方面,涉罪未成年人回歸社會(huì)需要一個(gè)和諧的環(huán)境,如果在被害人強(qiáng)烈反對(duì)的情況下,檢察機(jī)關(guān)仍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不僅可能激化矛盾、引發(fā)不穩(wěn)定因素,而且對(duì)于涉罪未成年人順利回歸社會(huì)也不利。《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guī)定》規(guī)定,“對(duì)于決定附條件不起訴可能激化矛盾或者引發(fā)不穩(wěn)定因素的,人民檢察院應(yīng)當(dāng)慎重適用。”也就是說,被害人的意見對(duì)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有重要的影響。這也符合“雙向保護(hù)原則”,以避免執(zhí)法的片面性。
實(shí)踐中,檢察機(jī)關(guān)會(huì)盡可能地鼓勵(lì)、說服涉罪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通過認(rèn)罪認(rèn)罰、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把保護(hù)被害人對(duì)附條件不起訴的救濟(jì)權(quán)轉(zhuǎn)化為事前對(duì)其權(quán)益的關(guān)注和尊重,在做好釋法說理的同時(shí),盡最大可能依法滿足其回歸正常生活的需要,包括物質(zhì)、精神損失獲得補(bǔ)償,相關(guān)困難得到解決等。因此,促使被害人對(duì)涉罪未成年人諒解或雙方達(dá)成和解,就成為檢察機(jī)關(guān)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前的重要工作,實(shí)踐中便呈現(xiàn)出附條件不起訴制度與刑事和解制度結(jié)合適用的局面,二者往往相互影響,在過程中互為條件,在法律后果上相互印證。需要指出的是,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和解中,不是只看或者重點(diǎn)關(guān)注是否賠償?shù)轿?而是更注重促進(jìn)涉罪未成年人從認(rèn)知到情感的社會(huì)化,真正起到實(shí)質(zhì)性的喚醒良知的作用。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只要有和解的誠(chéng)意,即使無力賠償,檢察機(jī)關(guān)也可以通過司法求助等方式予以解決。
記者: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整體適用情況怎么樣?下步重點(diǎn)工作是什么?
史衛(wèi)忠:從法律確立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以來,檢察機(jī)關(guān)對(duì)符合條件的涉罪未成年人積極適用,2015年以來,適用人數(shù)逐年上升,2015年至2019年,適用人數(shù)分別為3779人、4455人、5681人、6624人、7463人,占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總?cè)藬?shù)的比率(簡(jiǎn)稱“附條件不起訴適用率”)分別為6.04%、8.00%、10.06%、12.15%、12.51%。特別是2020年以來,最高檢指導(dǎo)各地檢察機(jī)關(guān)堅(jiān)持依法應(yīng)用盡用原則,前11個(gè)月對(duì)未成年人決定附條件不起訴9401人,附條件不起訴適用率達(dá)19.9%,同比上升7.8個(gè)百分點(diǎn)。
同時(shí),附條件不起訴考驗(yàn)期間因違反相關(guān)規(guī)定或者重新犯罪被提起公訴人數(shù)保持在較低水平,2015年至2019年分別為99人、141人、134人、183人、233人,被重新提起公訴人數(shù)占附條件不起訴總數(shù)的比率基本保持在2.3%至3.2%之間。2020年前11個(gè)月,附條件不起訴后重新起訴232人,占附條件不起訴人數(shù)的2.47%,反映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整體適用情況良好,且隨著適用人數(shù)不斷增加,教育挽救和監(jiān)督考察效果非但沒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
下一步,我們將以發(fā)布本批指導(dǎo)性案例為抓手,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附條件不起訴工作。一是提高附條件不起訴案件質(zhì)量。準(zhǔn)確把握適用附條件不起訴的條件,嚴(yán)格規(guī)范適用程序,推動(dòng)解決調(diào)查報(bào)告形式化、同質(zhì)化等問題,進(jìn)一步提升所附條件的針對(duì)性。二是合理提高附條件不起訴適用率。對(duì)符合附條件不起訴條件的案件,依法積極適用,尤其是對(duì)做相對(duì)不起訴處理或者法院判處一年及以下有期徒刑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較多的地方,加強(qiáng)跟蹤指導(dǎo),加大適用力度,維護(hù)好未成年人合法權(quán)益。三是加強(qiáng)對(duì)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調(diào)研分析。研究適用條件、合理范圍,為進(jìn)一步完善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提供檢察經(jīng)驗(yàn)和智慧。
記者:在附條件不起訴工作工作中,未成年人檢察社會(huì)支持體系能夠發(fā)揮什么作用?
史衛(wèi)忠:從發(fā)布的指導(dǎo)性案例可以看出,做好附條件不起訴工作,不僅要依托于專業(yè)司法隊(duì)伍的構(gòu)建,也有賴于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社會(huì)支持體系建設(shè)。這幾件指導(dǎo)性案例,一個(gè)共同的特點(diǎn)就是,檢察機(jī)關(guān)注重在個(gè)案辦理每個(gè)環(huán)節(jié)中,主動(dòng)爭(zhēng)取、整合相關(guān)社會(huì)力量的支持參與。如有的在審查逮捕、審查起訴中,全程引入司法社工落實(shí)社會(huì)調(diào)查、跟蹤幫教等特殊程序;有的在依法訊問、調(diào)查核實(shí)中,聘請(qǐng)心理專家開展人格甄別、犯罪心理分析等基礎(chǔ)性工作;有的在適用認(rèn)罪認(rèn)罰、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中,借力律師、監(jiān)管人員等實(shí)施認(rèn)罪教育、矯治教育等措施;有的在做好案件后半篇文章中,爭(zhēng)取團(tuán)委、婦聯(lián)、民政、教育、關(guān)工委等部門支持,建立未成年人犯罪預(yù)防機(jī)制等。堅(jiān)持在辦案中推進(jìn)社會(huì)支持體系建設(shè),在推進(jìn)社會(huì)支持體系建設(shè)中促進(jìn)辦案,以有效的溝通做到靶向發(fā)力,以密切的協(xié)作實(shí)現(xiàn)優(yōu)勢(shì)互補(bǔ),以資源的整合實(shí)現(xiàn)多贏共贏,最大限度體現(xiàn)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更大程度凸顯以人民為中心的司法追求,最終實(shí)現(xiàn)司法辦案“三個(gè)效果”有機(jī)統(tǒng)一,有效推進(jìn)未成年人保護(hù)社會(huì)治理,推動(dòng)形成黨委領(lǐng)導(dǎo)、政府支持、檢察監(jiān)督、社會(huì)協(xié)同、公眾參與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社會(huì)化支持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