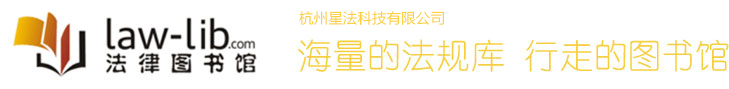資料圖 鐘心宇攝
正義網(wǎng)北京6月21日電(見習(xí)記者郭璐璐)河南鄭州的田女士正陷入一場離婚風(fēng)波,在焦心孩子撫養(yǎng)和房產(chǎn)分割問題的同時,她還格外擔(dān)心這兩年丈夫因?yàn)楣窘?jīng)營、還房貸等欠下的債務(wù)。“這些債務(wù)我該不該還?如果還,應(yīng)該還多少?”在夫妻債務(wù)承擔(dān)的問題上,田女士的心中有著太多疑惑。
不僅是田女士,實(shí)踐中深受夫妻共同債務(wù)困擾的人不在少數(shù),因此在網(wǎng)絡(luò)上關(guān)于“保護(hù)共債共簽”、“夫妻財(cái)產(chǎn)制度立法完善”、“夫妻債務(wù)制度立法完善”的呼聲不斷。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其中將相關(guān)司法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上升為法律,至此關(guān)于夫妻共同債務(wù)的立法完善落定。
“民法典構(gòu)建了立體的夫妻共同債務(wù)認(rèn)定制度,相關(guān)規(guī)定不僅能有效解決‘被負(fù)債’問題,還能有效避免‘假離婚、真逃債’問題,使債權(quán)人和非舉債配偶的合法權(quán)益得到有效保護(hù)和平衡。”不過,受訪專家也表示,由于夫妻債務(wù)問題異常復(fù)雜,在司法實(shí)踐中,應(yīng)及時制定出臺相配套的司法解釋及審判指導(dǎo)政策,統(tǒng)一執(zhí)法尺度,為相關(guān)民事活動和行為時提供正向的指引。
從婚姻法“24條”到民法典立法
針對日益突出的“假離婚、真逃債”問題,2003年12月,最高法出臺婚姻法司法解釋(二),其中第二十四條規(guī)定債權(quán)人就婚姻關(guān)系存續(xù)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fù)債務(wù)主張權(quán)利的,應(yīng)當(dāng)按夫妻共同債務(wù)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quán)人與債務(wù)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wù)的除外。這一度被作為裁定夫妻共同債務(wù)的重要法律依據(jù),在具體適用時飽受爭議。
西南政法大學(xué)民商法學(xué)院副教授朱凡表示,該規(guī)定有助于減少損害債權(quán)人利益的情況,但一定程度上也引發(fā)了對債務(wù)不知情、未受益配偶合法權(quán)益受損的情形,有人甚至?xí)摌?gòu)夫妻共同債務(wù)。“對債權(quán)人非常有利。”北京市律師協(xié)會婚姻與家庭法律專業(yè)委員會秘書長付鵬博說,實(shí)踐中非舉債配偶很少能完成舉證,原則上就需要和舉債配偶一起對外承擔(dān)無限連帶清償責(zé)任,即使離婚也無法解脫,這就出現(xiàn)了“被負(fù)債”的情況。
夫妻一方“非法舉債”或“虛假舉債”導(dǎo)致對方“被負(fù)債”的情況頻出。為此,2017年2月,最高法公布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的補(bǔ)充規(guī)定》,提到對于虛假債務(wù)、一方因賭博、吸毒等引發(fā)的不法債務(wù),第三人主張權(quán)利的,不得判定為夫妻共同債務(wù)。不過,這并未能徹底解決“被負(fù)債”問題,關(guān)于婚姻法“24條”的爭論沒有停止。
2018年1月,為進(jìn)一步明確夫妻共同債務(wù)的司法認(rèn)定,最高法發(fā)布了《關(guān)于審理涉及夫妻債務(wù)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guān)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8年司法解釋),規(guī)定夫妻一方在婚姻關(guān)系存續(xù)期間以個人名義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fù)的債務(wù),債權(quán)人以屬于夫妻共同債務(wù)為由主張權(quán)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債權(quán)人能夠證明該債務(w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chǎn)經(jīng)營或者基于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在受訪專家看來,2018年司法解釋是個重要的轉(zhuǎn)折點(diǎn),“轉(zhuǎn)為對非舉債配偶相對有利”。該司法解釋實(shí)施兩年多來,非舉債配偶“被負(fù)債”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夫妻債務(wù)問題引發(fā)的社會矛盾得到明顯緩解,同時也為通過立法解決完善夫妻共同債務(wù)問題提供了有力支撐。
今年5月,民法典高票通過,其中對夫妻共同債務(wù)問題進(jìn)行了規(guī)定。“這是把司法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上升為法律,是對2018年司法解釋的肯定和接受,對夫妻共同債務(wù)的認(rèn)定進(jìn)入了法典化階段。”受訪專家評價(jià)說,民法典在認(rèn)真總結(jié)審判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反復(fù)調(diào)研論證的基礎(chǔ)上,對夫妻共同債務(wù)認(rèn)定、舉證等問題做出規(guī)定,構(gòu)建了立體的夫妻共同債務(wù)認(rèn)定制度,有助于統(tǒng)一法律適用,避免司法實(shí)踐中對夫妻共同債務(wù)認(rèn)定出現(xiàn)困難和混亂。
平衡債權(quán)人與非舉債配偶的權(quán)益
依據(jù)民法典,夫妻雙方共同簽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認(rèn)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負(fù)的債務(wù),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關(guān)系存續(xù)期間以個人名義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fù)的債務(wù),屬于夫妻共同債務(wù)。夫妻一方在婚姻關(guān)系存續(xù)期間以個人名義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fù)的債務(wù),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wù);但是,債權(quán)人能夠證明該債務(w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chǎn)經(jīng)營或者基于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上述規(guī)定是明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負(fù)債務(wù)屬于夫妻共同債務(wù),充分尊重民商事法律確定的一般交易原則,肯定了夫妻雙方獨(dú)立的民事主體地位。”陜西省人民檢察院第六檢察部主任彭艷妮認(rèn)為,同時強(qiáng)調(diào)夫妻共同債務(wù)形成時共債共簽,可以引導(dǎo)民事活動主體規(guī)范交易行為,從源頭上防止夫妻一方“被負(fù)債”,也能防止債權(quán)人因無法舉證屬于夫妻共同債務(wù),遭受不必要損失。
在婚姻關(guān)系存續(xù)期間,單方舉債行為該如何認(rèn)定?單方舉債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wù)?“關(guān)鍵是要區(qū)分是否屬于為家庭生活日常需要所負(fù)的債務(wù)。”受訪專家坦言,由于何謂“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法律上沒有進(jìn)行相應(yīng)的界定,司法實(shí)踐上也缺乏相對確定的標(biāo)準(zhǔn),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與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同一問題的不同方面,需要結(jié)合案件情況進(jìn)行綜合判斷。
“應(yīng)當(dāng)指普通家庭和個人日常生活必要、必須發(fā)生的項(xiàng)目和開支,即具有普遍性、共性的項(xiàng)目,如衣食住行消費(fèi)、醫(yī)療教育、子女撫養(yǎng)、老人贍養(yǎng)等。”同時付鵬博認(rèn)為,可考慮“金額”問題,法官應(yīng)結(jié)合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債務(wù)人家庭收入等具體情況,行使自由裁量權(quán)綜合認(rèn)定債務(wù)性質(zhì),但要注意避免剛性的、一刀切的金額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
在舉證責(zé)任分配方面,民法典規(guī)定了債權(quán)人舉證的權(quán)利。“債權(quán)人主張屬于夫妻共同債務(wù)的,應(yīng)當(dāng)提供證據(jù)證明夫妻共同分享了舉債所帶來的利益,或舉債實(shí)際上基于夫妻共同意思作出的。”彭艷妮認(rèn)為,這符合法律關(guān)于證明責(zé)任分配規(guī)定,也相對較好的平衡了債權(quán)人與未舉債配偶的權(quán)益。
考慮到債權(quán)人對夫妻內(nèi)部關(guān)系舉證存在一定的客觀難度,為了防止糾紛發(fā)生后的舉證困難,她建議債權(quán)人在借款發(fā)生形成債權(quán)債務(wù)關(guān)系時,盡量堅(jiān)持夫妻共債共簽的做法,以保護(hù)自身合法權(quán)益。
不僅在舉證方面對債權(quán)人提出了要求,民法典關(guān)于夫妻共同債務(wù)的規(guī)定也對法院審理此類案件提出了更高要求。“法院應(yīng)根據(jù)具體案情,做好釋明和事實(shí)查明工作,合理分配好各方對案件相關(guān)事實(shí)的證明責(zé)任,平衡好各方當(dāng)事人的利益。”受訪專家強(qiáng)調(diào)說,可采取“順藤摸瓜”的方式,追蹤、查明涉案債權(quán)債務(wù)的實(shí)際去向和具體用途,只有在窮盡手段無法查明、無法認(rèn)定的情況下,才能由債權(quán)人最終承擔(dān)舉證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建議及時出臺相關(guān)配套司法解釋
陜西省檢察機(jī)關(guān)曾辦理過涉夫妻債務(wù)的抗訴案件。據(jù)彭艷妮介紹,在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債務(wù)人在外有大量借款,多個債權(quán)人起訴要求債務(wù)人配偶承擔(dān)償還責(zé)任,后法院判決債務(wù)人配偶共同承擔(dān)還款責(zé)任。債務(wù)人配偶向檢察機(jī)關(guān)申請檢察監(jiān)督,檢察機(jī)關(guān)審查查明,債務(wù)人配偶雙方在舉債期間已長期分居,債務(wù)人在外借款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認(rèn)為判決要求債務(wù)人配偶承擔(dān)責(zé)任,不符合婚姻法第四十一條規(guī)定。基于此,檢察機(jī)關(guān)提起抗訴,法院再審判決舉債人配偶不再承擔(dān)還款責(zé)任。
“因涉及夫妻共同債務(wù)認(rèn)定糾紛問題,申請檢察機(jī)關(guān)抗訴的案件確實(shí)存在,但這類案件在陜西檢察機(jī)關(guān)全部抗訴案件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彭艷妮分析說,主要原因在于司法實(shí)務(wù)部門已經(jīng)注意到這一問題,2018年司法解釋公布后,最高法發(fā)布《關(guān)于辦理涉夫妻債務(wù)糾紛案件有關(guān)工作的通知》,提出已經(jīng)終審的案件,甄別時應(yīng)當(dāng)嚴(yán)格把握認(rèn)定事實(shí)不清、適用法津錯誤、結(jié)果明顯不公的標(biāo)準(zhǔn)。比如,對夫妻一方與債權(quán)人惡意串通坑害另一方,另一方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無端背負(fù)巨額債務(wù)的案件等,應(yīng)當(dāng)依法予以糾正。
“將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有助于統(tǒng)一法律適用,避免司法實(shí)踐中對夫妻共同債務(wù)認(rèn)定出現(xiàn)困難和混亂。”至于民法典施行后的辦案重點(diǎn),受訪專家認(rèn)為應(yīng)關(guān)注以下問題:審查債務(wù)是否真實(shí)發(fā)生、是否合法有效,防止未具名一方配偶因非法債務(wù)或虛假債務(wù)“被負(fù)債”;正確界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標(biāo)準(zhǔn),對于是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多種因素綜合判斷;注意舉證證明責(zé)任分配,要重視對之前裁判規(guī)則特別是證明責(zé)任分配規(guī)則帶來的改變,正確理解,準(zhǔn)確適用;案件辦理過程中,可以適當(dāng)?shù)貜?qiáng)化司法機(jī)關(guān)職權(quán)探知,確有必要的,可依當(dāng)事人申請或依職權(quán)主動調(diào)查案件事實(shí)。
“不能止步于民法典,還應(yīng)持續(xù)關(guān)注研究夫妻共同債務(wù)問題,以應(yīng)對將來可能發(fā)生的新情況、新問題。”付鵬博曾代理過多起涉夫妻債務(wù)案件,其中不乏借款部分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產(chǎn)經(jīng)營的情況。他說,應(yīng)重點(diǎn)研究、關(guān)注部分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產(chǎn)經(jīng)營,非舉債配偶的責(zé)任承擔(dān)問題。如果部分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該怎么處理才公平、合理?是否能規(guī)定非舉債配偶對與其有關(guān)聯(lián)的債務(wù)連帶承擔(dān)清償責(zé)任為宜?認(rèn)定是應(yīng)非常審慎,否則,仍易引發(fā)非舉債配偶“被負(fù)債”問題。
“應(yīng)繼續(xù)圍繞非舉債配偶責(zé)任承擔(dān)方式和責(zé)任財(cái)產(chǎn)范圍去研究,同時繼續(xù)深挖民法典夫妻共同債務(wù)相關(guān)規(guī)定的內(nèi)涵和外延以及非舉債配偶以夫妻共同財(cái)產(chǎn)為限補(bǔ)充承擔(dān)有限連帶責(zé)任是否具可行性,相關(guān)研究成果可通過司法解釋等方式指導(dǎo)司法實(shí)踐。”受訪專家補(bǔ)充說,對歷史遺留的結(jié)果顯失公平的夫妻共同債務(wù)案件,特別是非舉債配偶因被大額負(fù)債陷入生存、生活、生產(chǎn)困境的案件,相關(guān)部門應(yīng)予以研究,做好新法與舊法的銜接適用問題,比如可設(shè)定合理的銜接過渡期限。符合再審條件的,當(dāng)事人也可以申請?jiān)賹彙?/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