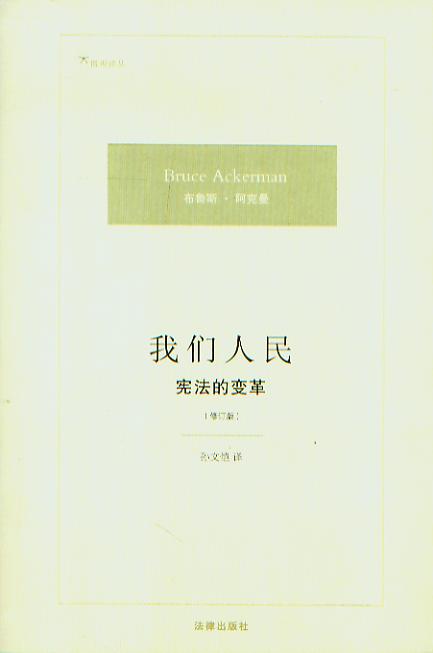
總統領導權的勃興
在上一章中,我對那種把20世紀30年代的新政改革視為憲法傳統之再現的觀點提出了質疑。雖然費城會議以及約翰·馬歇爾為現代政府開創了某些憲法根
基,但現代政府的所有重要決定還是由20世紀的美國人作出的。如果說有誰是現代積極干預的國家政府的奠基人,那是富蘭克林·羅斯福而不是詹姆斯·麥迪遜;如果說有哪個議會是積極干預的國家政府的創建者,那是新政國會而不是費城會議;如果說有哪個法官為積極干預的國家政府作出重要貢獻,那是休斯而不是馬歇爾。
我并不否認,建國時期開創的憲法改革先例有助于人們以歷史的眼光看待新政。但只有在更廣闊的背景下,我們才能發現二者之間的巨大相似之處。20世紀30年代也像18世紀80年代一樣,一群信奉國家中心主義的改革者都不愿按照原有的高級法創制規則行事——他們當然也沒有完全拋棄此前規范人們政治生活的所有制度。20世紀30年代像18世紀80年代一樣,改革者都在原有的制度材料之外締造了全新的立法模式——而且這些立法模式最終都獲得了人民的支持、取得了高級法的地位。20世紀30年代像18世紀80年代一樣,改革者締造的、推動憲法改革的制度花車,在人民投票選舉的推動下,都最終到達了憲法改革成果的鞏固階段。從這些甚至更多層的意義上講,新政革命都把開國元勛們
以非常規手段實現人民主權的做法,創造性地運用到了20世紀。
可是,忽視19世紀改革所作出的憲法貢獻是不正確的。不僅因為林肯和賓格漢姆所處的時代比華盛頓與麥迪遜距現在更近,而且還因為重建時期的共和黨人不得不面對那些曾經困擾著新政者甚至現在還困擾著我們的一些重要問題:怎樣改造建國時期憲法設計的制度,以使之能夠有效地表達出內戰后美國人日漸強烈的國家意識?共和黨人動用了包括總統領導權、分權以及國家選舉等手段,以贏得選民支持他們發動的基本憲法改革。對這些手段的創造性運用不僅構成了憲法第13、14修正案真正的憲法基礎,而且也為新政革命提供了具有決定意義的歷史先例。
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論點,那么它就為我們更深入地評論以及重構現有的憲法觀點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主流觀點認為,判決洛克納案的聯邦最高法院是由一群傻瓜或無賴法官(或傻瓜加無賴)組成的。恰恰相反,我認為審理洛克納案的聯邦最高法院做了大多數法官在大多數時間內都會那么做的工作:以重建共和黨人確定的本意去解釋憲法。現在,洛克納案的判決已不再是什么好的法律,因為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人否定了共和黨人確立的憲法價值觀,而不是因為面對大蕭條的共和黨人法院嚴重背離了這種傳統的憲法價值觀。由于在很多地方都提到了這種論點,因此我想在此立即提出第二個重要的問題:羅斯福新政是否可以被視為合法地改革了共和黨人確立的憲法傳統、實現了人民主權的合憲行動呢?
像我們此前對待重建那樣,上述問題的完整答案也需要我們對兩個全然不同的階段進行一番研究。誠如推動憲法第13修正案和第14修正案獲得批準的動力存在著很大差別一樣,羅斯福新政也經歷了兩個不同的階段。20世紀30年代,整個國家為大蕭條的憲法含義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而在20世紀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憲法意蘊則成了人們爭論的焦點。兩個階段所追求的基本目標是一致的——逐漸放棄自由放任主義,向積極干預的國家政府轉變。由于對這兩個時期展開詳細的討論將占去本書的很大篇幅,因此我已另行撰文探討了推動憲法變革的外部關系。在此,我把討論的重點放在舊式法院和20世紀30年代的新政之間的沖突上。
“傳統再現的神話”視新政和舊式法院之間的這場斗爭為一場巨大的不幸、一種時間上的浪費。相形之下,我更想強調這場斗爭對于提高民主討論、民主決定的質量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像重建時期那樣,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沖突非常明確地向美國人民提供了若干可供選擇的憲法改革方案。政府各部門之間沖突的最終結果,是重塑了美國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系。而這種對政府和人民之間關系的重新定位,要比沒有發生上述沖突的情況下更審慎、更民主。
我將從探尋1933年羅斯福前往華盛頓就職時,他到底贏得了多少人民授權說起。這一問題遠比主流觀點所作的推論要復雜得多。一旦我們認清了這一問題的復雜性,我們就會很容易地評價舊式法院所發揮的積極作用。雖然舊式法院在羅斯福第一任期內對新政的司法抵制激怒了新政者,但它卻提請廣大民眾注意:民主黨的動議提出了一個遠非華盛頓的政治精英們所能解決的問題;而保守法官所詮釋的傳統憲法價值觀是否還有保留的必要性,應由人民作出最終的決定。
摘自:(美)阿克曼著《我們人民:憲法的變革(修訂版)/博觀譯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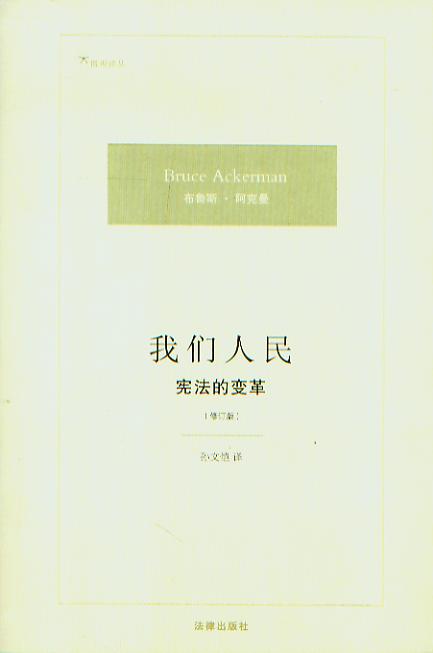 總統領導權的勃興
總統領導權的勃興